朱熹与丽娘

十多年前曾看过黄梅戏连续剧《朱熹与丽娘》,一直很喜欢里面的剧情,只是唱段记不太清楚了,暂且以小说的形式来说这段故事看过多多提供唱段资料,貌似这个版本的小说与剧情有出入,丽娘最后是为保全朱熹名声而因火自焚。
- 书名 朱熹与丽娘
- 类别 故事
- 装帧 平装
- 开本 16
- 出自 黄梅戏连续剧
传说
朱熹与丽娘的传说
朱熹长期生活的武夷山流传着一个朱熹与丽娘的这样一个传说故事,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五曲溪创办了一所书院,叫做武夷精舍,当时四方求学的弟子非常多,形成了道在武夷的这种壮观。
他有一天讲完学到溪畔去散步,前面走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跪在他的脚下,请朱熹收她为徒,朱熹感到非常地突然,因为朱熹从来就没有招收过女学生,所以他一直不肯,在这个女子的一致要求下,朱熹只有破例地收了这个女生,那这个女生白天跟武夷精舍诸生一起上课,晚上就陪伴朱熹著书,他帮助朱熹研磨,抄书了,久而久之两个人就有一种感情。
当时武夷山到武夷书院去要过一条河,有一个摆渡的艄工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他就跟朱熹说你招的这个女生是一个狐狸精,朱熹感到非常突然,简直不能相信,他说你如果不信的话,等到她这个女子疲倦的时候,她两个鼻子就会露出两支牙块来,过了几天朱熹著书,连续著书三四个晚上,这女子也陪他了三四个晚上,然后有一天晚上这个女子非常的困了,就在朱熹的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快睡着了,突然之间她的鼻子两个牙块就露出了,朱熹就把这个牙块拔掉,拔掉以后这个女子就变成了一条狐狸,窗外这个艄工就在那儿大笑,朱熹这时候非常气愤,就把他的朱笔向这个艄工投去,这个艄工就变成了一个乌龟,向九曲溪畔走去,朱熹非常眷恋这个女子,就是叫做胡丽娘,非常眷恋她,就把她埋葬在朱熹武夷精舍的后面的山上,所以这个山上现在还有一个狐狸洞。
朱熹和狐狸精
南宋淳熙十年,朱熹辞官回到武夷山,在碧水萦绕的五曲溪畔建起了武夷精舍。那四方的学一子,慕朱夫子大名纷纷前来,求学听经。
朱熹住在清隐岩下的茶洞房。这里奇峰秀水,丹岩翠壁,一道道瀑布从天游峰上"哗哗哗"地流泻下来,像一片片雪花撤落在雪花泉里。泉外长满了一丛丛青青的岩茶,山风一吹过呀,清香扑鼻。朱熹专心做他的学问,饿了吃一块冷地瓜;渴了喝一杯浓茶;冷了跺跺脚取暖;困了舀一瓢泉水洗脸提神。他每天讲学著述到深夜。
日落月起,花开花谢。朱熹独居深山,冬去了,春天又来了,月缺了,十五又圆了。朱熹在寂寞中更加怀念起早逝的妻子口他把盏对着明月,遥祭刘夫人,不时又自饮几盅,借酒来浇愁哩,一天黄昏,日头刚落山,朱熹正对着满天的晚霞吟诗作赋,忽然听到门外传来"先生,先生"的呼唤声,忙出门一看,_见茶洞外的独木桥上站着一位女子,正笑吟吟地朝这边走来口那女子一步一颤的,震得独木桥吱扭吱扭地摆着;忽然,朱熹看那女子脚下一滑,差点儿绊倒,就急忙上前扶着她从桥上走了下来。
"你是何人,家住哪里,为何来到此地?"
"我姓胡,名叫丽娘,家住在五曲河对面。因仰慕先生的才学,特来拜夫子为师,请受学生一拜。"丽娘望着朱熹,一边说着,一边就向他施礼参拜。
朱熹又惊又喜,心想:我平生虽有弟子数百,却从未收过女流。但这女子端庄识礼,又如此求学心切,想来并非俗人,不妨就收下她吧!朱熹扶起丽娘,问过她平日的读书情况,就将她引人书房,向她讲授起四书五经来了。
这丽娘确实机灵,聪明过人,不一会儿。就把先生讲的全都记住了,而且能背会诵,对答如流。
朱熹一时高兴,搬出自己的一大叠诗稿给丽娘看。丽娘见诗稿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绝句,画了许多红圈红杠,就说:"蒙先生不弃,就让学生把诗稿誊写一遍吧!嗯?"丽娘见朱熹笑着点了点头,就磨墨提笔,在纸上喇喇地写了起来。
朱熹默默地站在一旁,见丽娘书法如行云流水,笔触潇洒娟秀,不禁呆住了:这女子果有才气,今天收为门生,日后也不枉费老夫一番心血呀!
丽娘专心致志地誊写,刚抄完一篇,抬头见朱熹正凝神地看着自己,那颗心立时涌上了胸口,脸也红了,朝他轻轻地喊了声"先生",就低下头来。朱熹心头一热,马上察觉出自己举止有失,慌忙支支吾吾地走开了。
从这以后,丽娘风雨无阻,天天晚上来到朱熹的书房。她读遍了四书五经,替朱熹誊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文,还常常陪先生吟诗作画到深夜哩。
丽娘不但才学过人。而且聪明贤惠,体贴先生:朱熹饿了,她就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竹笋香菇面;朱熹渴了,她又送来一盘甜蜜蜜的武夷香桃李;六月酷暑,她为先生摇扇送凉;早春寒夜,她又为先生起火取暖。
这一来,朱熹的著述越来越多,文思越来越敏捷。丽娘的柔情体贴,使朱熹感到温暖与欢乐,有时又思绪缕缕,他爱丽娘的才学风貌,爱她的温柔多情。每天一早,丽娘走了,他就觉得孤单,总是巴望日头快落山,月儿早点升起。
这天傍晚.朱熹因思念丽娘,去平林渡口散步等她。忽听得有人唤了声"朱夫子",回头见是摆渡的乌老头两口子。朝他招呼着走来,忙停了脚步。这两口子长着三角脑袋,鼓着双金鱼眼睛,男的又高又大,女的又矮又小,一身穿戴黑不溜秋的,活像一对丑八怪似的。
乌老头朝朱熹瞅了瞅,摇摇三角头,伸长又黑又细的脖子说:"哎呀,朱夫子,看你这气色不好,定是中了邪呀!"
乌老婆子也阴阳怪气地叫:"是呀,是呀,中了邪呀,这邪气入骨,要大难临头罗!"
朱熹问:"此话怎讲?"
乌老头说:"你可知每天晚上到你房的女子是谁?"
朱熹反问:"你说她是谁?"
乌老头说:"她是武夷山的狐狸精哩!"
"啊!"朱熹大吃一惊,又急忙问:"狐狸精到我书房为何?"
乌老婆一子又接上话说:"谋你的才学,-唉,糊涂呵,还谋你祖传的玉碗,"朱熹听了心里纳闷:白从来了丽娘,我笔下生花,学业精进;那祖传的玉碗么?丽娘每晚都要擦上几遍,小心地供在香案上、她岂有谋财之意呢?好端端一个正经女子,怎么是狐妖?"胡言乱语!"朱熹厉颜正色地说着,就拂袖而去了。
朱熹走近书房,推门一看,不知丽娘何时已在灯下为他缝补衣裳了,心里感到一阵温暖。他仔细端详。越觉得丽娘长得秀丽、端庄,那双巧手匕针走线,眼边嘴角含笑,更见脉脉含情,禁不住轻声地唤起丽娘的名字来。丽娘见先生深情地打量着自己,脸一红,心里头像有只小鹿在跳。她忙站起把补好的衣服披在朱熹身七,然后挑亮灯芯,摆好诗书,准备听先生讲课。
可是,朱熹哪有心思讲课呢?他虽不相信丽娘是狐狸精,但是摆渡佬的话像毒蛇一样死死缠着他,咬着他,搅得他心神不定。
丽娘一看先生脸色不好,忙问:"先生,看你这脸色,是不是身子不舒服了?"
朱熹慌忙摇摇头,说:"哦哦,没有,没有……"
丽娘问:"那你?"
朱熹说:"丽娘……我今天遇到摆渡人了……"
"啊!"丽娘暗暗一惊,好久好久,她才抬起头来,对朱熹说:"先生,你不要听信谗言,不要听信谗言呀!"
朱熹见丽娘眼里滚下两串亮晶晶的泪珠,忙上前劝说:"丽娘,我不信,不信那些谗言。"从这以后,朱熹和丽娘结成一对恩爱失妻。一天,朱熹出门散步,就觉得有人在他背后嘀嘀咕咕;走进学堂,又见弟子们在议论狐夫人……
朱熹正闷闷不乐,又遇到那两个尖头三角脸的摆渡佬。
乌老头说:"大胆的朱熹,老夫好言相劝,你非但不听,反而与狐狸结为夫妻了。"
乌老婆子又怪声怪气地帮腔:"哎呀,唉唉,朱夫子如你不信,不妨照我和老头的办法一试。"说着,两口子在朱熹耳边叨咕了一阵,转眼不见了。
朱熹听愣了,心如乱麻地回到家里,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他只好拿起朱笔,坐在案前批改文章。丽娘见先生没有人睡,也陪着他坐到天明。一连两夜都是这样。到了第三天晚上,丽娘实在困极了,上下眼皮一直打架,只好伏在书案上睡着了。四更天时,朱熹打了个磕睡醒来一看,就被眼前一片光亮惊呆了:只见一对碧绿透明的玉筷从丽娘的鼻孔里伸了出来T他慌忙上前想喊醒丽娘,只听得"恍当"一声,玉筷被碰落地上,闪出一只狐狸的影子,一晃就不见了。接着丽娘醒过来。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心痛欲裂,站也站不住,眼泪像断厂线的珠子簌簌地滚了下来。她哭着说:"先生,我们要分别了,我虽有心陪伴夫终身,但事到如今,也不得不走了。一先生,丽娘走了,无人问寒问暖,无人添衣送茶,你要自己珍重,珍重呀!"
朱熹心如刀绞,紧紧地抓住丽娘的手说:"丽娘,你不能走,不能走呀!"
丽娘摇摇头,痛苦地说:"先生,我是武夷山修炼于年的狐狸精。因为仰慕先生的才学,知道先生的寂苦,所以每晚渡河来到书房,照料先生起居,陪伴先生读书。不料,平林渡的摆渡佬,那一对害人的乌龟精,想谋先生的玉碗和丽娘的玉筷,曾跟我斗法,被贬在那儿摆渡。现在他们恶言中伤,拨弄是非.使我俩分散,生离死别,我恨、我恨呀!先生,如今丽娘道行已破,玉筷离身,归宿洞穴,我该到南螟靖里长眠去了……先生呀,丽娘不能跟你百年到老了,只能在高高的南晖靖里把你相望……"
丽娘泪水涟涟,与朱熹难分难舍。忽然空中忽隆隆滚过一阵闷雷,在一阵旋风里闪过一对黑影;丽娘泣不成声,指着窗外黑影喊:"先生,是它们,毁了丽娘,就是它们拆散了我们恩爱夫妻呀:……"
朱熹气得咬牙切齿、浑身打颤,抄起朱笔扔向窗外,只见朱笔像燃烧的箭直飞而去;两个摆渡佬立时"啊"地叫了一声,就变回一对乌龟原形,慌忙地往九曲上游跑去……等朱熹回过头时,丽娘已经不见踪影了。
朱熹发狂似地追出房门,对着空旷的山野大声喊着:"丽娘-一!丽娘归来!丽娘归来!"
天渐渐地亮了.未熹沿着崎岖的山路,急匆匆地爬上隐屏峰,只见南溟靖门开满了五颜六色的山花,花丛里静静地躺着一只美丽的狐狸。朱熹痛似肠断,他采一朵鲜花,哭一声,又采一朵鲜花又哭一声,慢慢地把狐狸掩埋在南螟靖里。民间传说,他还在洞前立了一个"狐氏夫人"的石碑。从此,武夷人就把南溟靖叫做"狐狸洞"了口直到如今,凡是往来武夷山的游客,都一定要爬上狐狸洞去,看一看这位多情的丽娘!
至于那两只慌忙逃窜的乌龟精,刚爬八曲上水狮旁边.就再也爬不动了,变成一对石龟一一那就是我们现在乘竹排游九曲时所见到的上、下水龟。那小龟之所以歪歪斜斜地趴在大龟背上,传说那是矮小的乌老婆子中了朱笔后,骨头变软了,爬不动了,就由老乌头背着跑。到了水狮地方,一头栽倒溪边,就死了口至今还一上一下地趴在水里呢!
黄梅戏连续剧
《朱熹与丽娘》获得第九届"飞天奖"、第七届"金鹰奖"和"攀枝花奖"
故事大概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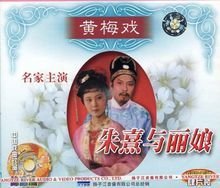 黄梅戏连续剧《朱熹与丽娘》
黄梅戏连续剧《朱熹与丽娘》 去也终须去,住也何处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胡丽娘含着泪水望着远处自己的闺房一片火光,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母亲严蕊填的卜算子词,从今以后那个活泼可爱的胡丽娘死了,她一定要找到朱熹那个迂腐的老夫子,替母亲年轻时的那段公案讨回公道,也替自己讨回公道。
风光秀丽的武夷山上,紫阳书院,朱熹正聚精会神地给他的学生们讲他的朱程理学,他那认真专注的态度被一位女子看在眼里,她是今天上午刚被朱夫人从山下集镇上买来的,朱夫人很喜欢这个乖巧的女孩,当问及她的姓名时,她微笑着说:"莫问奴。"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朱夫人没有觉出这名字的奇怪,只是笑了笑。
"雨外黄昏花外晓,催得流年,有恨何时了?"问奴手中拿着刚剪下的桃花来到朱熹的书房,她想等一个时机心平气和地跟夫子说个明白:他那样做毁了她的一生,那个可恶的贞洁牌坊,她年纪轻轻怎么能承受这么重的枷锁?
书房里寂静无声,她刚把桃花插在花瓶里,只吸到有人赞叹:"好一个人面桃花!"问奴抬起头,原来是朱熹。
问奴笑言:"堂堂夫子大人也会取笑人"。
朱熹哈哈大笑:"夫子也是人,夫子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你是刚来的?叫什么名字?"
"奴婢叫莫问奴。"
"莫问奴,莫问奴"。朱熹拈着胡须慢慢地踱着方步,他盯住问奴的眼睛:"很有禅意的名字,能说说出处吗?"
"奴婢姓莫,原没有名字,常从这个东家到那个东家之间飘荡,总有人来问奴家的身世和身价,所以就干脆叫问奴了。"
"哦,我说呢,小小年纪会取这么个名字 。你可曾认得字?"想着严蕊现在已是中年,不会变成这么小到这儿来,再说她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女儿。(其实他哪里知道,严蕊在入狱之前已经生下了小丽娘了。)
"只认识一点。"问奴怯怯地答道。
"你看这桃花妖艳动人,背一首有关桃花的诗给我听听!"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有一首是我以前的东家写的雨落桃花:明霞艳艳遮柳丛,玉人轻笑乱东风。春使妒催清明雨,殷红片片落泥中。"
"好诗!好诗!好记性!"朱熹鼓掌莞尔。"你去吧,闲时多读点书,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尽可以来问我。"
"谢夫子!"问奴拜了万福,转身走了。
朱熹对着问奴的背影愣了好久,她太像她了,多年前自己的偏见使得她入狱遭受了非人的折磨,自己实在有愧于她,但苦于没有机会当面致歉。哎,他看了看桌上的桃花,轻轻念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问奴出了书房门,抑制不住心中的慌乱,向外跑去,刚才差点就要问他了,不知道为何竟然不忍心开口,自己不是非常恨他的吗?
春去秋来,问奴到朱府已有半年,每天耳濡目染,听到的都是一些"灭人欲,存天理"之类的话,而自己却无法反驳这些理论,难怪母亲在遭受非人的磨难之后还是那么崇拜朱熹,并要求自己按照道德礼教去接受那个所谓的贞洁牌坊。
这一天,晚风吹着庭前的绿竹,淡淡的;月儿照着万物,融融的。问奴独自在小径上漫步。到这儿以后,自己就像被一堆乱丝缠绕,分不出头绪,一方面朱熹是推自己于火坑中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他的众多理学又是人们尊崇的楷模,而且他的渊博的学识又很值自己去学习。正胡思乱想中,忽听远处隐隐传为笛声,笛音如泣如诉,似在悲叹自己的怀才不遇,待走近时,笛声突然高亢起来,如裂石穿云,霜天里沙漠飞扬,渐渐地遮住了远处的山脉,笛声转为平缓,慢慢地,静静地,似把天上的明月吹落,随后寂静无声。
问奴听到这儿,忍不住长吁了一口气,吹笛人听到声响,转过身来,竟是朱熹,他的眼睛亮亮的,那亮亮的一定是泪光,想到这,问奴的心里无来由一阵绞痛,忽然又被自己的这种心痛吓了一跳,自己本该恨他的,可刚才听了笛音之后,她知道自己失败了,她不仅不恨他,反而欣赏他了,朱熹见问奴站在那儿,定了定神,笑问:"这么晚了还不睡?看你穿得这么单簿,当心夜凉。"话刚说完,朱熹竟被自己的言语吓了一跳,对一个侍婢说这么亲切的话可是前所未有的。
"谢夫子关心,我是被笛音牵来的,夫子吹得真好,改日夫子可要教我。"问奴由衷地说。
"没吵着你吧,可听懂了?教你可以,不过我要看你有没有天赋。"他想起了初见她时,叫她背桃花诗的情形,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起来。
"夫子吹的曲调是不是《驻马听》?"
"不错,你可听出了什么?"
"裂石穿云,玉管宜横清更洁。霜天沙漠,鹧鸪风里欲偏斜。凤凰台上暮云遮,梅花惊作黄昏雪。人静也,一声吹落江楼月。"问奴轻声说道。
"好,真不愧是知音,你这徒弟我收定了。"朱熹情不自禁地抓住问奴的手,问奴的俏脸一红,转身害羞而去,朱熹望着她的背影愣了好久。
第二天一大早,朱夫人便来到问奴的房间,问奴慌忙施礼下跪,朱夫人伸手拦住了她,拉住她的手,好一阵端详:"果然是越看越俊俏,越看越可爱。你我二人结为姐妹,可好?"
问奴大惊,慌忙摇手:"使不得,使不得。"
"有什么使不得的?连夫子都时常夸你天资聪慧呢。"朱夫一脸和气。
"夫子也这么说吗?"问奴的脸上有点迷茫。
"是啊,是啊。夫子常念起你呢!哎!"说完,朱夫人长叹了一声。
"夫人为何叹息?"问奴问道。
"哎,是这么回事,我与夫子结发已有三十年,可惜的是膝下竟无一子,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我已年竟半百,此生再是无缘得子,我对不起夫子,黄泉路上我是无颜以对朱家的列祖列宗啊。"朱夫人说完已泣不成声。
"夫人不必伤心,只要你们二人恩爱就好,管他什么孝不孝的,没有孩了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夫子他敢怪罪与你?"问奴一边安慰,一边为朱夫人鸣不平。
"夫子对我是不错,可是我心里总觉着对不起他。"朱夫人说完重新拉起问奴的手:"问奴啊,你看你从小没了爹娘,总是这样流离失所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留在这儿,与我同侍夫子如何?"朱夫人好不容易才说出口。
"这。。。。。。"问奴犹豫了,此事若发生在刚上山时,自己断然不答应不说,还要骂个痛快,但现在,夫子与夫人待自己确实不错,在这儿学了很多做人的道理,难得的是夫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以算得上是半个知音,自己已由原来仇恨转而爱慕了,如果不是昨晚听到夫子的笛声,问奴再也不会相信自己会爱上夫子。而且自纵火离家出走后,常听路人说起"烈女贞妇胡丽娘"的故事,所以现在即使有家难回了,胡丽娘的身份将在人们的传说中消逝,想到这里,问奴不由落下泪来。
"你是嫌夫子老了吗?"朱夫人见问奴半天没说话,又见她流下了眼泪,以为问奴不同意。
"啊,不,不,不,夫子正当壮年,事业如日中天,我是想着自己身世凄苦,地位卑下,配不上夫子。"问奴慌忙解释。
"你看你,不许说什么地位卑下的话,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亲姐妹了,这亲事可就定下了。回头我差人送些上好的布匹过来,替你做几套像样的衣服。"朱夫人开心地说。
"啊,不行。"
"为什么不行?"
"夫子说:'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问奴狡黠地笑道。
"哈哈。。。。。"一向稳重的朱夫人禁不住大笑起来:"好,好,我回去叫夫子重写《治家格言》!"
夫子与问奴的婚礼是在红叶烂漫的季节举行的,参加婚礼的人只有朱夫人,他们不想过于张扬,因此夫子的学生们只知道新师母很漂亮,只是无缘一睹芳容。
婚后的问奴与夫子相敬如宾,与夫子也和睦相处,武夷山的各条小径上都留下了他们欢快的足迹,山林里常回荡着他们欢乐的笑声。
日月交替,斗转星移,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冬天,问奴顺利产下一可爱的男婴,朱熹老来得子,兴奋不已,满月一到,他的学生们也齐来道贺,朱府里喜气洋洋。问奴抱着孩子出现在堂前,她这是第一次见朱熹的学生与同僚。学生中有一个叫白蕤的忽然觉是新师母很面熟,他悄悄对同学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新师母。"
一旁的同学讥笑他:"别做梦了,我们都是初次见新师母,除非你半夜三更翻墙。。。"
白蕤的脸急得通红:"我发誓我决不是在这儿见到她的,哦,想起来了。"
他悄声对同学耳语道。同学大吃一惊:"不太可能吧,你确定没认错!"
"决没认错,我和她是一条巷子长大的,我们小时候常在一起做游戏的。"白蕤说得很坚决。
"你们在争论什么?"旁边的同学和朱熹的好友都围过来。
"他说新师母就是胡丽娘,夫子亲手提笔批示的烈女楷模!"此言一出,满堂大惊。那
边的胡丽娘也听到了吵闹声,走近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白蕤大声说道:"丽娘,原来你没死啊,你娘都要急疯了。"
问奴一听有人叫她的名字,大吃一惊:"你是谁?"
白蕤说:"我是小蕤,从小和你一块儿长大的,你记不得了?"
丽娘一看自己竟然被别人认出来了,急得满脸通红,大声喝叱:"你是谁,竟然在这儿胡言乱语,我不认识你。"说完转身回房去了。
朱熹急问白蕤是不是真的?白蕤说:"我发誓,我说得句句是实,天下间没有长得如此相像之人,她们的嗓音都是一样的,老师若不信,我回去把严妈妈叫来。"
"好,好,快去,快去!"朱熹不相信眼前的事实,这么无天理的事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客人们不欢而散,朱熹来找问奴问个明白,任凭朱熹说破了喉咙,她就是不开口,只是趴在床上不停哭泣。
朱熹只好叫朱夫人去问,在朱夫人面前,问奴不再隐瞒,她承认自己就是胡丽娘:"事已至此,我已无话可说,夫人打我骂我都可以,只求夫人留下我,我要看着我的孩子长大。"
朱夫人满脸泪痕:"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妇守夫节,是你做人的根本,你这样一来,不仅害了夫子,也害了你的孩子啊,你叫他长大以后如何做人?"
"我。。。。。我。。。。。!"胡丽娘无言对对。
"你还是待在这儿不要出去,等你娘来了以后再从长计议吧。"朱夫人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三天以后,严蕊赶到,她难以相信自己的被火吞去女儿竟然还活着。刚到紫阳书院,她就迫不及待喊:"丽娘,丽娘,你在哪儿?"朱夫人出来迎接,把严蕊带到后院,问奴的房间。
母女重逢,肝肠寸断,朱夫人也在一旁陪着流泪。
朱熹满脸愧疚地看着严蕊:"十几年了,想不到我们竟是在这样的状况下相见,我早就想跟道歉!"说完对着严蕊鞠了三鞠躬。
严蕊说道:"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我早已不怨恨夫子,只恨我教子无方,丽娘对不起夫子的金笔题字啊!"
一旁的朱夫人忽然说道:"胡丽娘,你女儿怎么会是狐狸的娘?"
话如惊雷,严蕊看了看自己的女儿:"是啊,你怎么是狐狸的娘?你不是我的女儿,
我女儿早死了!"
一旁的胡丽娘不敢相信这句话竟然出自自己的亲生母亲之口,她看了一眼朱熹,朱熹一脸的冷漠,再看看朱夫人,满目狰狞,早已不是以前的那个和蔼可亲的,自己视同母亲的人了。
她大喊一声:"天灭我,不可活啊。"说完跑出门去。
背后传来阵阵锣鼓声:"抓狐狸娘啊,它往山上跑了。""别让它跑了,以后出来害人啊,抓狐狸精!"
胡丽娘奋身往山上跑着,后面的追喊声越来越近,忽然前面的悬崖挡住了去路,她看着背后越来越近的人群,纵身跳下了悬崖。人群跑到了山顶,没有找到胡丽娘的身影,只听悬崖下传来一阵歌声:
我是芙蓉刚出水,
我是紫燕待双飞。
只怨冬日冷风紧,
夜黑黑,路漫漫,
风雨把花摧。
人生难得入佳境,
无边的黑夜何时听惊雷?
你是春风到古镇,
吹动死水浪花扬。
秽语中伤抛身后,
雪霏霏,路茫茫,
只把深情藏。
冰雪遮住春山暖,
摧我振翅飞翔。
摧我振翅飞翔....
分集剧情
第一集:胡丽娘自幼与柳家公子定亲,但柳家公子早年夭折。这样丽娘就成了未嫁的寡妇,柳家与胡家都是官家,看重礼教。当时,社会盛行名士朱熹的程朱理学,这就要求丽娘要嫁给已去世的"丈夫"。朱熹亲自赐匾,柳家也为她修盖"贞节楼"。丽娘本不肯,但不想让自己的母亲背上"养女不教"之名,且其母骗她百日后可回家,才勉强答应。丽娘对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不满,在朱熹的匾额下写下了"愿朱子福佑早得贵子"。为此事,在柳家大闹一场,此时丽娘才知要在这里守一辈子。而丽娘的母亲知道女儿性情倔强,定然不肯,于是到了柳家,一面劝说丽娘,一面想搬来与女儿同住。与母亲一番交谈后,知道了母亲原来就是严蕊。严蕊本是在籍官妓,昔年曾被诬与太守有染。朱熹便将太守革职,严蕊入狱。严蕊在狱中写下了一首《卜算子》(最后两句:"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新太守看到此诟员外也前来祝贺。丽娘知道后,非常气愤,想冲到大堂,使真相大白,以便让想拿自己骨灰邀功请赏的人空欢喜。胡丽娘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胡夫人苦苦相劝,当说到朱熹很可能被杀,丽娘和朱熹平时的柔情蜜意都是假的吗。丽娘愣住了,她发现假已慢慢成了真,恨不知何时变成了爱。丽娘随朱夫人出来,朱熹说自己蒙圣宠,时有封赠,只有两次加官不当。一次是二十年前,听信谣言,冤责严蕊,自己深为内疚;这次胡家痛失爱女,自己又加官,于心不安,将赏银给了胡丽娘的母亲。丽娘十分动情,不停地哭,朱熹误以为是夫人是向问奴说了做妾之事。朱夫人与朱熹谈论问奴的婚事,想将问奴嫁出去,以免日后生祸。而朱熹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问奴了,决意收问奴为二房。夫人苦劝无果,正欲说出问奴身份,又怕说出丽娘身份后,朱熹将她赶走,使丽娘未死之事公之于众,于朱家不利。这时,丽娘自己出来,说清了一切。"你走吧。""我该走了。""不,不能让她走。一个孤身女子,你让她往何处去啊,夫子。""让她走!走出武夷!走出XX!走出XX!走出...咳咳...""我为什么走出武夷!""武夷山是我朱熹宣讲理学的地方,岂能...""哼,武夷是属于你的吗?不,我就是不出武夷!我胡丽娘第一次爱上的就是武夷!"胡丽娘扔下自己绣的手帕,离开了,万世流芳带走了朱熹的自画像。朱熹思念丽娘,几日未曾下饭,终于决定亲自寻找问奴。而丽娘也在溪边等朱熹,她的歌声将朱熹引了来。她听到"问奴"她赌气躲在树后,当听到"丽娘",她出来了。顾不得许多了...朱夫人也出来找朱熹了,看到他们在一起,道:"夫子...夫子,为了朱氏大业,你们...你们不能啊......"
第四集:身体一直不好的朱夫人谢世,朱熹娶丽娘续弦。朱熹与丽娘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一段时光,在此期间,丽娘产下一子----载儿。不料风波又起,在载儿抓周那日,丽娘被前来拜师的柳家人认出,欧知县和柳家人为出气,想凭借此事扳倒朱熹。严蕊听到丽娘嫁给朱熹,十分吃惊,表示不相信丽娘会嫁给朱熹,但所见情形又不似假,便亲赴武夷,一探究竟。严蕊见到丽娘,告诉事情已经败露。此时欧知县、柳员外、冯察院到了,朱熹先在大堂应付,后来严蕊抱着载儿出来,以"我本狐狸娘,托化嫁朱郎。今日尘缘了,常归洞府旁。"暂时将事掩过。不料,丽娘在山上又被发现,丽娘为保朱熹和载儿,在狐仙洞外引火自焚。"在这场人心与道心,人欲与天理的征战中,朱熹创立的理学竟成了禁锢和摧残他自己的桎梏。然而,他的心无时不在啜泣,无时不在悸动,年复一年,此恨无穷。带着刻骨铭心的爱,煎熬在痛苦而又追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