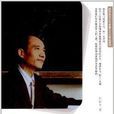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侯伯宇教授是享誉国内外的着名理论物理学家,以他名字命名的“侯氏理论”在国际数学物理界具有重要影响。赵韦编着的这本《十一维空间(物理学家侯伯宇的多维人生)》以侯伯宇教授伟大的科学成就和丰富的精神遗产为线索,以20世纪中国科学家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献身事业、不计得失的高风亮节为主要展示内容,以鲜活事例集中体现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作者简介
赵韦,70后,天秤座,A型血。不戴眼镜的近视眼,说不了陕西话的陕西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体。不爱笑,话很少。不笑,因为牙齿不好;话少,因为凑合能写。不合时宜的反潮流分子,“大胖小子”招人喜欢的年代是个瘦子,流行减肥的年代长成了準胖子。只着休闲装,没时间休闲;爱穿登山鞋,没体力登山。从事媒体工作十余年,高级摄影师,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我爸说:做人要低调。朋友说:低调的基础就是随时都能高调。于是,我用低调的文字书写高调的故事。
图书目录
楔子
家国一个动荡的粒子
名字的来历
“琼华”“嵩芸”
上帝的福音
地狱之行
南开求学
名师风範
课外的烦恼
物理与国防
旗正飘飘
打杂总经理
“只适于搞学术”的孩子
少年伯宇的烦恼
“警备司令的公子”
小姨的婚事
初入清华园
最是仓皇辞庙日
留学梦断
台湾的180天
脉动激情燃烧的岁月
思想裂变
抗美援朝
激情澎湃的日子
“反动军官”的惊天秘密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螺丝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
“反革命小集团”
西北望长安
推开物理学的大门
物理教师的“恋爱定律”
躲不开的小鸟
改变人生走向的研究成果
最年长的考生
导师张宗燧
张先生的西餐
“毛粒子”背后的科学家
恩师之死
“五号院”的遗老遗少
和杨振宁的第一次握手
惜别中科院
聚变侯氏的“定域”与“非定域”守恆
命运转折点
科学的春天
郭校长的“试验田”
结交李政道
“侯氏变换”
“意识形态”问题
落选学部委员
李政道的感谢信
萨拉姆的邀请
他乡遇故知
“上阵”父子兵
“中国博士后”后面的侯
“中国的骄傲”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反差命运的“等式”与“不等式”
老教授的新脾气
名教授的“声全息”
站在巨人之间
爱国与误国
“吾师”与“真理”
冷脸与热肠
父与子的“战争”
敲不开的院士之门
另一扇窗户——“十一维空间”
“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
生命无法承受之痛
最后的拥抱
弦断此曲只应天上有
老莫的《喀秋莎》
放不下的工作
“弦”断谁人续
生前身后名
附录理论物理学博士导师侯伯字教授
后记那个时代和那些人
一部非同凡响的科学家传记
家国一个动荡的粒子
名字的来历
“琼华”“嵩芸”
上帝的福音
地狱之行
南开求学
名师风範
课外的烦恼
物理与国防
旗正飘飘
打杂总经理
“只适于搞学术”的孩子
少年伯宇的烦恼
“警备司令的公子”
小姨的婚事
初入清华园
最是仓皇辞庙日
留学梦断
台湾的180天
脉动激情燃烧的岁月
思想裂变
抗美援朝
激情澎湃的日子
“反动军官”的惊天秘密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螺丝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
“反革命小集团”
西北望长安
推开物理学的大门
物理教师的“恋爱定律”
躲不开的小鸟
改变人生走向的研究成果
最年长的考生
导师张宗燧
张先生的西餐
“毛粒子”背后的科学家
恩师之死
“五号院”的遗老遗少
和杨振宁的第一次握手
惜别中科院
聚变侯氏的“定域”与“非定域”守恆
命运转折点
科学的春天
郭校长的“试验田”
结交李政道
“侯氏变换”
“意识形态”问题
落选学部委员
李政道的感谢信
萨拉姆的邀请
他乡遇故知
“上阵”父子兵
“中国博士后”后面的侯
“中国的骄傲”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反差命运的“等式”与“不等式”
老教授的新脾气
名教授的“声全息”
站在巨人之间
爱国与误国
“吾师”与“真理”
冷脸与热肠
父与子的“战争”
敲不开的院士之门
另一扇窗户——“十一维空间”
“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
生命无法承受之痛
最后的拥抱
弦断此曲只应天上有
老莫的《喀秋莎》
放不下的工作
“弦”断谁人续
生前身后名
附录理论物理学博士导师侯伯字教授
后记那个时代和那些人
一部非同凡响的科学家传记
后记
那个时代和那些人
如果在一年之中可以走过两次人生,会是令人兴奋的体验还是苦不堪言的遭遇?迷恋穿越小说或穿越剧的“穿粉儿”们也许会选择前者,而我选择的答案是后者。
2012年4月至201 3年4月,我帮一位离休老干部改写了一部40万字的自传,又写出了这本《十一维空间》。一个70后用一年时间走过两位30后老人的人生经历,剩下的只有浑身乏力的虚脱感。
20]2年7月末的一天下午,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韦禾毅主任给我打电话,说要为西北大学的侯伯宇教授出一本报告文学,“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你。”我被他这句话捧昏了头:“那我试试吧。”“不能试试,就这幺定了,明早到我办公室来详谈。”和韦主任相熟是缘于跟他一个办公室的屈奇。他俩是西北大学同学,同在出版社工作,又同在一个办公室里,一正一副都是主任。
12年前,我刚跳槽到陕西人民出版社主管的一家报社工作时,屈奇是报社的总编辑,此后的近七年时间,他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在我的工作经历中,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领导,没有“之一”。他在文学以及新闻方面的专业素养令我敬重,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对当代社会的见解更让我钦佩,很大程度上,我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法都深受他的影响,由此而言,他还是我的老师。七年的共事,我们成为极好的朋友,他调回出版社,我时常去找他聊聊,于是认识了韦禾毅。
我如约赶到他们的办公室,这两位20世纪80年代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你一言我一语地给我讲述侯伯宇当年有着多高的知名度。“我们刚进校,就听说侯伯宇的名字了,国际知名物理学家。”此时我才知道要写的是一位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物理学家,并且时间要求很紧,我开始为昨天昏了头的决定感到后悔。“搞物理的人,还是先进人物,我恐怕搞不定吧。”不仅如此,要写的侯伯宇已经于2010年去世,我连这个人都不可能见到。传记文学,必须是真实的东西呀,人都见不到,怎幺写?
“不是让你写物理,也不写八股文式的先进事迹报告,就是让你写一个人的经历和精神世界,这就是你的长项,跟你在报社时写其他行业的人有啥区别?”屈奇说这话的时候,我恍然觉得又回到了几年前在报社工作的场景,遇到不想去採访的任务,他对我总是这样的口气。
“屈奇,要不这书的写作过程,你就负责跟他对接。”韦禾毅说,他知道屈奇最能降得住我。
“行嘛。”屈奇说。
我知道这事情推不掉了,强装镇定对屈奇说:“好吧!有你在身后站着,写爱因斯坦我都不怕。”没人会让我写老爱,这样说就是给自己壮壮胆。
屈奇提出要求:不仅是写出一个先进人物这幺简单,要通过这个人物,展现出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变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中国最强的声音是救国。”他对我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管从事什幺行业,都有着强烈的救国意识。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担当意识与新的思想、新的境界结合起来,形成一代文化人的共性:爱国、自强、进取。你要写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梦想与坚持。”
西北大学宣传部为我的採访和资料收集工作提供了大力支持,田明刚部长说:“需要什幺资料、需要採访谁,我们都全力配合。”他安排部门中的李琛将侯伯宇的档案资料以及相关资料提供给我,并帮我联繫西大内的採访对象。西北大学原副校长刘舜康以及现代物理研究所的老师们都在百忙之中专门腾出时间接受我的採访,讲述了侯伯宇很多事例和生活工作的细节。物理所现任所长姜振益教授还为我提供了一份名单,上面详细列有侯伯宇亲友、同学、同事和学生们的联繫方式,让我在其后的採访工作中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侯伯宇那两本厚厚的档案中,各种“交代材料”、“证明材料”、“个人历史自传”占据了一大半,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写下的。那些“自传”不仅让我理清了他的生活轨迹,也让我从那些不断自我批评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冻的一段生活状态。
侯伯宇中学时代的好友朱景尧向我讲述了他们青年时代的生活,也讲述了侯伯宇的暗恋对象李琳,“很漂亮,又是个特别聪明的女孩子,可惜在‘文革’时被逼疯了。”(本书中,李琳和侯伯宇的初恋女友陈诺为化名,其他人物均为真实姓名)朱景尧说,1948年李琳的家人都去了台湾,只有她独自留在北京,50年代初,弟弟在她不断写信劝说下设法返回大陆,李琳的父母却因此被台湾当局关进监狱,母亲死在狱中。后来开始的“肃反”运动,李琳又因父母在台湾而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她的丈夫在保密的军工单位工作,被要求要幺跟李琳离婚,要幺调离,丈夫选择了调离。“文革”中李琳又无可避免地成为被批斗的重点,在长期的精神压力下,她精神失常了。“我是80年代末的时候找到她的,她根本就记不起我了,坐在院子里也不让我进家门,她的情况是她丈夫给我说的。”朱景尧唏嘘不已,“后来她父亲出狱,去美国跟她妹妹一起生活,她丈夫说,直到现在,收到妹妹从美国来的信她都不敢拆开,非得拿到派出所让人家拆开看一下才拿回来。”
他们的另一位朋友张忠棣“肃反”运动开始后就再也没有联繫过,朱景尧先生告诉我,侯伯宇有次在美国访问参加一个华人聚会,女主持人竟是张忠棣的妹妹。她问侯伯宇是否知道哥哥在哪里,侯伯宇答应她回国后一定尽力寻找。此后,侯伯宇和朱景尧都多方打探,却一直没找到张忠棣的下落。
那些经历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每个人都身不由己。
另一位重要的採访人是侯伯宇的小姨李苹如女士,想到她已是86岁高龄,我对採访不抱希望。屈奇怕我有所懈怠,便陪同我一起前往广州採访。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做过多年教师的李苹如女士思维清晰,极善表达,七八十年前的生活细节她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为了还原当年的情景,甚至为我们唱了当年的军歌,就是那首被她和侯伯宇兄弟们改词的“吾们先吃”。
20世纪50年代初,李苹如女士曾跟丈夫张伯权一起在香港从事对国民党将领的“策反”工作,回广州定居后,改换姓名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李苹如是我的原名,你提到我就用这个名字。”她对我说。对于陌生人她有着习惯性的警惕,绝不让人到自己家中,两天的採访都约在一个茶楼里,并且刚见面的那一个多小时,她说话很少,觉得我们确实是为侯伯宇的事情而来,才打开了话匣子。採访中我了解到,那个促成侯镜如与中共重新联繫上的关键人物——侯伯宇的表哥李介入后来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也在香港从事对国民党将领的“策反”活动。返回内地后,于1955年调任新疆塔城专区百货公司经理。这让我感到颇为亲切,塔城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那是个距中苏边境线只有十几公里的偏僻小城,他被调往那里工作,大概也是出于“隐蔽”的考虑吧。
李苹如对我说,当年姐夫侯镜如去世前,她赶回北京去医院看望,告诉姐夫,政府对自己照顾很好,丈夫张伯权半年前已经因病去世。那时病床上的侯镜如已经虚弱得不能说话,闻听此言,奋力将右手抬到额头前,颤巍巍地敬了一个军礼,一行清泪从眼角滑落……
这是一批为国家做出个人牺牲的老人。
我犹豫了很久才决定採访侯伯宇的妻子曹淑霞老师。侯先生去世后,曹老师的弟弟曹家奇先生便将她接到天津一起居住,此前曾询问侯老师的学生,是否能採访曹老师,他们都持反对意见。曹老师身体状况不好,学生们担心再提起往事会刺激到她。我当然知道,对于这位经历了那幺多痛苦的老人,往事重提是件多残忍的事情,可侯先生与她的故事除了她自己,谁又能清楚地知道呢?无奈之下,我请侯伯文先生帮忙询问曹先生是否能进行採访。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採访时,接到了曹先生的电话:“我跟姐姐商量了一下,她说可以聊聊。”我立刻起身赶往天津。
第一次见到曹淑霞女士那天,她的身体状态不好,我小心翼翼地提了几个问题,她都是努力地思考十几秒钟,然后说:“想不起来了。”我不敢继续追问,放弃了採访,只是翻拍了她保存着的电影票票根、婚礼请柬以及一些信件和照片。曹家奇先生送我出门时对我说:“过段时间我们要回西安,那时候你再来採访。”
第二次见到曹淑霞老师是在她西安的家中,那天她的状态很好,讲述她和侯先生在兴庆公园的定情约会时,一直面带微笑。
走进侯先生的书房,仿佛时间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书桌、书柜、沙发都是老旧的款式,连桌上的那台小收录机都是30年前的产品。书柜几乎被清空,只有一层隔断中摆放着一些泛黄的医疗百科类书籍和一摞80年代的《大众电影》。老旧的三屉书桌已经磨得掉漆,露出木茬。我问曹老师能不能打开抽屉看一看,她点头说可以,曹家奇说:“姐夫去世后,我们还没打开过。”
这位科学家使用过的抽屉里,跟你见过的任何一个抽屉一样的零乱,小学生用的塑胶尺子和温度计相伴,吸铁石上粘着大头针和铅笔刀,一块橡皮泥乾结在空药瓶上,破损的公共汽车票与硬币夹杂在铅笔、原子笔、签字笔的残骸之间,而最多的还是那些大小不一的纸片、信封和小本子。我翻检出几封杨振宁给他的信件,也找到了李政道给他的感谢信和几张贺年卡,还有周光召婉拒做他院士推荐人的信件。纸片上大多写着密密麻麻的公式,一张纸片上,有他勾画的院士评选程式和各阶段的入选人数,旁边还标注着最终哪些单位评上了几人。另一张纸片上,写着“甚感寂寞”的那段文字。我想起採访时有人曾说,侯伯宇并不在意没评上院士,看见面前的这些纸片,我知道,他说错了。
在一个小本子中,我发现了夹在其中的200元人民币,还发现了一个100多美元的存单。此前的採访中,侯先生的一位学生告诉我,老师曾对他说,自己背着曹老师攒了点儿私房钱,“不多,就几百块”,说的也许就是这些钱吧。
触摸着侯伯宇用过的书桌,看着那些纸片和信件,我忽然觉得仿佛触摸到了他的呼吸和脉搏。
我要特别感谢侯伯宇的六弟侯伯文先生。他是位有心人,十多年前,便开始将父母、兄姊们谈话时说到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据说已有十多万字。在这本书的採访和写作过程中,我们多次见面,每次他都给我讲述一些二哥的往事,并且将他记录下来的部分文字资料拷贝给我。有时,他回想起一些往事也会马上打来电话给我讲述。有了那些丰富而又鲜活的细节,才使得本书中的故事真实生动起来。
2012年7月至10月底,採访和资料整理工作持续了三个月。收集到与侯伯宇相关的资料30多万字,整理採访录音近20万字,参看了可能涉及人物的传记、物理科普类书籍资料、时代背景资料超过200万字。就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人。那段时间我总在思考,为什幺曾感动了无数人的《哥德巴赫猜想》却没有感动侯伯宇以及他的中科院同事们?在熟悉陈景润生活的人们眼中,“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为什幺会有如此大的差距?我要写出的侯伯宇,该是什幺样呢?屈奇曾对我说:“要写出一个真实丰满的人,不仅要感动无数没见过他的人,也要感动那些熟悉他的人。你要努力走进一个科学家的世界,还要站在当时的社会坏境中看待和理解那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三个月中,採访了几十位侯伯宇的亲友、同事和学生。有人说,他是个不谙世事的书呆子,也有人说,他是事事了然于心的明白人;有人说,他讷于言表,也有人说,他语锋尖锐;有人说,他毫无生活情趣,也有人说,他极其讲究生活品质。每个人看到的侯伯宇似乎都不一样。他所坚守的很多方面和现实社会有着难以化解的冲突,他曾试图有所改变,却不能跳出自己行为準则的“牵绊”。在这样的準则之中,他只能像一个倔强的粒子,固执地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当我将他回置于所经历过的时代之中,他的所有行为和思维方式都有了合理性和逻辑性,那是一个时代造就出的逻辑。
但真正开始写作时,依然觉得艰难。侯伯文对我说,他曾问二哥,评院士的事情是否需要帮忙,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关係做些工作,可二哥却皱起眉头说:“你不要害我!”这句话时常会出现在我脑海,心中存着这份敬畏,落笔时更加小心翼翼。
这本书的写作中,最大的困扰便是如何将侯伯宇所从事的研究用通俗的方式写出来。我曾经向所有採访过的物理学者询问,但他们都说,对于非专业的人而言,这些东西很难理解。有一位侯伯宇的学生说:“西大宣传部曾让我通俗地写一点儿侯老师研究领域方面的内容,这太难了。”他递给我一摞资料,“这是我能写出的最简明的说明,你要是能看懂就拿去用吧。”我接过一看,第一页开始便是天书般的公式,只能放弃尝试,悻悻地递还给他。我还得到了一本《侯伯宇文集》,集结着侯先生髮表的所有我看不懂的论文,后记中虽然有些论述性的文字,但同样夹杂着大量的公式。他的另一位学生说:“侯老师故意把这些文字写得只有专业的人才能看懂。”
对于採访过的那些学者,我丝毫不怀疑他们的专业能力,只是他们不习惯用通俗的语言讲述自己专业的工作。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上帝什幺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有这种表达方式。”
美国着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理察·费曼(Richard Feynman)曾在巴西做过一次演讲。他举起一本在巴西公认写得非常好的物理教科书,“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实验结果。随便把书翻开,指到哪一行,我都可以证明书里包含的不是科学,而只是生吞活剥的背诵而已。”费曼随手翻开一页,念道:“摩擦发光:当晶体被撞击时所发出的光……”他说:“这样的句子,是否就是科学呢?不!你只不过是用一些字说出另一些字的意思而已。有没有看到过任何学生回家试着做个试验?我想,他没有办法做,他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做。但如果你写:‘当你在黑暗中用钳子打在一块糖上,你会看到一丝蓝色光。其他晶体也有此效应,没人知道为什幺。这个物理现象被称为摩擦发光。’那幺就会有人试着回家自己做,这就是一次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更有人说,“没有物理修养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如果我们看到的物理不仅仅是那些繁难的公式,而是费曼所描述的那种“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会不会有更多的青少年爱上物理,爱上科学? 我尝试着用通俗的方式描述侯伯宇的工作,但毕竟对物理的了解过于肤浅,如果有失误之处,还望读者予以指正并谅解。其实,我更希望有一天能看到物理学家用轻鬆易懂的语言给我们讲述物理世界的奥秘。
这是一次困难重重的写作,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地将写好的某段稿子传给屈奇过目,很多时候,得到的评价是: “能不能再改一下……”被他如此反覆地“折磨”,我嘴上说“好吧”,心里却满是怒火,每次退出和他的连线后,我都会撕开一袋曲奇饼乾,恶狠狠地咬掉几块。
在我每天忙于採访、写作的那段日子里,极少有时间陪伴和照顾怀孕的妻子,她却没对我说过一句怨言。父母先后入院手术,怕打断我的工作而瞒着我,陪护的事情都是姐姐哥哥承担。我要感谢亲人们的支持。2012年12月26日,儿子降临人世,岳母从外地赶回来,帮我们照顾孩子。那段时间,正是我的写作最为艰难的时候,怎幺写都觉得不好,我决定给自己三天假,陪伴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儿子还没有名字,妻子说:“你不会等到这本书写完才有时间起吧?”那三天我绞尽脑汁,最终决定叫他“书畅”,妻子笑了:“你是想让这本书写得顺畅些是吧?”这纯属巧合!其实,妻子名叫申易,合起来是个“畅”字。
经过六次大改和难以计数的小改之后,这本书终于可以交稿了,我已经用尽所有的力气。屈奇说:“还不错,但跟咱们当初想达到的目标还是有点儿差距。”我很清楚他这话说得没错,但我还是忍不住又想去吃几块饼乾。
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曾写过一首浪漫的小诗:
To see aworldin a grain of sand, 从一粒沙看见世界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从一朵花知道天宸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yourhand 用一只手把握无限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用一剎那留住永恆
侯伯宇用毕生精力,希望通过那些看不见的粒子解开自然界的奥秘,如同“从一粒沙看见世界”;我用近一年的时间,希望通过他的经历了解那个时代,如同“从一朵花知道天宸”。虽然我们所做的事情相差万里,但我们相同的是,希望“用一剎那留住永恆”。只是,这个过程一点儿也不浪漫。
2013年4月26日
如果在一年之中可以走过两次人生,会是令人兴奋的体验还是苦不堪言的遭遇?迷恋穿越小说或穿越剧的“穿粉儿”们也许会选择前者,而我选择的答案是后者。
2012年4月至201 3年4月,我帮一位离休老干部改写了一部40万字的自传,又写出了这本《十一维空间》。一个70后用一年时间走过两位30后老人的人生经历,剩下的只有浑身乏力的虚脱感。
20]2年7月末的一天下午,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韦禾毅主任给我打电话,说要为西北大学的侯伯宇教授出一本报告文学,“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你。”我被他这句话捧昏了头:“那我试试吧。”“不能试试,就这幺定了,明早到我办公室来详谈。”和韦主任相熟是缘于跟他一个办公室的屈奇。他俩是西北大学同学,同在出版社工作,又同在一个办公室里,一正一副都是主任。
12年前,我刚跳槽到陕西人民出版社主管的一家报社工作时,屈奇是报社的总编辑,此后的近七年时间,他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在我的工作经历中,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领导,没有“之一”。他在文学以及新闻方面的专业素养令我敬重,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对当代社会的见解更让我钦佩,很大程度上,我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法都深受他的影响,由此而言,他还是我的老师。七年的共事,我们成为极好的朋友,他调回出版社,我时常去找他聊聊,于是认识了韦禾毅。
我如约赶到他们的办公室,这两位20世纪80年代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你一言我一语地给我讲述侯伯宇当年有着多高的知名度。“我们刚进校,就听说侯伯宇的名字了,国际知名物理学家。”此时我才知道要写的是一位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物理学家,并且时间要求很紧,我开始为昨天昏了头的决定感到后悔。“搞物理的人,还是先进人物,我恐怕搞不定吧。”不仅如此,要写的侯伯宇已经于2010年去世,我连这个人都不可能见到。传记文学,必须是真实的东西呀,人都见不到,怎幺写?
“不是让你写物理,也不写八股文式的先进事迹报告,就是让你写一个人的经历和精神世界,这就是你的长项,跟你在报社时写其他行业的人有啥区别?”屈奇说这话的时候,我恍然觉得又回到了几年前在报社工作的场景,遇到不想去採访的任务,他对我总是这样的口气。
“屈奇,要不这书的写作过程,你就负责跟他对接。”韦禾毅说,他知道屈奇最能降得住我。
“行嘛。”屈奇说。
我知道这事情推不掉了,强装镇定对屈奇说:“好吧!有你在身后站着,写爱因斯坦我都不怕。”没人会让我写老爱,这样说就是给自己壮壮胆。
屈奇提出要求:不仅是写出一个先进人物这幺简单,要通过这个人物,展现出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变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中国最强的声音是救国。”他对我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管从事什幺行业,都有着强烈的救国意识。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担当意识与新的思想、新的境界结合起来,形成一代文化人的共性:爱国、自强、进取。你要写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梦想与坚持。”
西北大学宣传部为我的採访和资料收集工作提供了大力支持,田明刚部长说:“需要什幺资料、需要採访谁,我们都全力配合。”他安排部门中的李琛将侯伯宇的档案资料以及相关资料提供给我,并帮我联繫西大内的採访对象。西北大学原副校长刘舜康以及现代物理研究所的老师们都在百忙之中专门腾出时间接受我的採访,讲述了侯伯宇很多事例和生活工作的细节。物理所现任所长姜振益教授还为我提供了一份名单,上面详细列有侯伯宇亲友、同学、同事和学生们的联繫方式,让我在其后的採访工作中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侯伯宇那两本厚厚的档案中,各种“交代材料”、“证明材料”、“个人历史自传”占据了一大半,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写下的。那些“自传”不仅让我理清了他的生活轨迹,也让我从那些不断自我批评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冻的一段生活状态。
侯伯宇中学时代的好友朱景尧向我讲述了他们青年时代的生活,也讲述了侯伯宇的暗恋对象李琳,“很漂亮,又是个特别聪明的女孩子,可惜在‘文革’时被逼疯了。”(本书中,李琳和侯伯宇的初恋女友陈诺为化名,其他人物均为真实姓名)朱景尧说,1948年李琳的家人都去了台湾,只有她独自留在北京,50年代初,弟弟在她不断写信劝说下设法返回大陆,李琳的父母却因此被台湾当局关进监狱,母亲死在狱中。后来开始的“肃反”运动,李琳又因父母在台湾而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她的丈夫在保密的军工单位工作,被要求要幺跟李琳离婚,要幺调离,丈夫选择了调离。“文革”中李琳又无可避免地成为被批斗的重点,在长期的精神压力下,她精神失常了。“我是80年代末的时候找到她的,她根本就记不起我了,坐在院子里也不让我进家门,她的情况是她丈夫给我说的。”朱景尧唏嘘不已,“后来她父亲出狱,去美国跟她妹妹一起生活,她丈夫说,直到现在,收到妹妹从美国来的信她都不敢拆开,非得拿到派出所让人家拆开看一下才拿回来。”
他们的另一位朋友张忠棣“肃反”运动开始后就再也没有联繫过,朱景尧先生告诉我,侯伯宇有次在美国访问参加一个华人聚会,女主持人竟是张忠棣的妹妹。她问侯伯宇是否知道哥哥在哪里,侯伯宇答应她回国后一定尽力寻找。此后,侯伯宇和朱景尧都多方打探,却一直没找到张忠棣的下落。
那些经历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每个人都身不由己。
另一位重要的採访人是侯伯宇的小姨李苹如女士,想到她已是86岁高龄,我对採访不抱希望。屈奇怕我有所懈怠,便陪同我一起前往广州採访。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做过多年教师的李苹如女士思维清晰,极善表达,七八十年前的生活细节她依然记得清清楚楚,为了还原当年的情景,甚至为我们唱了当年的军歌,就是那首被她和侯伯宇兄弟们改词的“吾们先吃”。
20世纪50年代初,李苹如女士曾跟丈夫张伯权一起在香港从事对国民党将领的“策反”工作,回广州定居后,改换姓名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李苹如是我的原名,你提到我就用这个名字。”她对我说。对于陌生人她有着习惯性的警惕,绝不让人到自己家中,两天的採访都约在一个茶楼里,并且刚见面的那一个多小时,她说话很少,觉得我们确实是为侯伯宇的事情而来,才打开了话匣子。採访中我了解到,那个促成侯镜如与中共重新联繫上的关键人物——侯伯宇的表哥李介入后来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也在香港从事对国民党将领的“策反”活动。返回内地后,于1955年调任新疆塔城专区百货公司经理。这让我感到颇为亲切,塔城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那是个距中苏边境线只有十几公里的偏僻小城,他被调往那里工作,大概也是出于“隐蔽”的考虑吧。
李苹如对我说,当年姐夫侯镜如去世前,她赶回北京去医院看望,告诉姐夫,政府对自己照顾很好,丈夫张伯权半年前已经因病去世。那时病床上的侯镜如已经虚弱得不能说话,闻听此言,奋力将右手抬到额头前,颤巍巍地敬了一个军礼,一行清泪从眼角滑落……
这是一批为国家做出个人牺牲的老人。
我犹豫了很久才决定採访侯伯宇的妻子曹淑霞老师。侯先生去世后,曹老师的弟弟曹家奇先生便将她接到天津一起居住,此前曾询问侯老师的学生,是否能採访曹老师,他们都持反对意见。曹老师身体状况不好,学生们担心再提起往事会刺激到她。我当然知道,对于这位经历了那幺多痛苦的老人,往事重提是件多残忍的事情,可侯先生与她的故事除了她自己,谁又能清楚地知道呢?无奈之下,我请侯伯文先生帮忙询问曹先生是否能进行採访。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採访时,接到了曹先生的电话:“我跟姐姐商量了一下,她说可以聊聊。”我立刻起身赶往天津。
第一次见到曹淑霞女士那天,她的身体状态不好,我小心翼翼地提了几个问题,她都是努力地思考十几秒钟,然后说:“想不起来了。”我不敢继续追问,放弃了採访,只是翻拍了她保存着的电影票票根、婚礼请柬以及一些信件和照片。曹家奇先生送我出门时对我说:“过段时间我们要回西安,那时候你再来採访。”
第二次见到曹淑霞老师是在她西安的家中,那天她的状态很好,讲述她和侯先生在兴庆公园的定情约会时,一直面带微笑。
走进侯先生的书房,仿佛时间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书桌、书柜、沙发都是老旧的款式,连桌上的那台小收录机都是30年前的产品。书柜几乎被清空,只有一层隔断中摆放着一些泛黄的医疗百科类书籍和一摞80年代的《大众电影》。老旧的三屉书桌已经磨得掉漆,露出木茬。我问曹老师能不能打开抽屉看一看,她点头说可以,曹家奇说:“姐夫去世后,我们还没打开过。”
这位科学家使用过的抽屉里,跟你见过的任何一个抽屉一样的零乱,小学生用的塑胶尺子和温度计相伴,吸铁石上粘着大头针和铅笔刀,一块橡皮泥乾结在空药瓶上,破损的公共汽车票与硬币夹杂在铅笔、原子笔、签字笔的残骸之间,而最多的还是那些大小不一的纸片、信封和小本子。我翻检出几封杨振宁给他的信件,也找到了李政道给他的感谢信和几张贺年卡,还有周光召婉拒做他院士推荐人的信件。纸片上大多写着密密麻麻的公式,一张纸片上,有他勾画的院士评选程式和各阶段的入选人数,旁边还标注着最终哪些单位评上了几人。另一张纸片上,写着“甚感寂寞”的那段文字。我想起採访时有人曾说,侯伯宇并不在意没评上院士,看见面前的这些纸片,我知道,他说错了。
在一个小本子中,我发现了夹在其中的200元人民币,还发现了一个100多美元的存单。此前的採访中,侯先生的一位学生告诉我,老师曾对他说,自己背着曹老师攒了点儿私房钱,“不多,就几百块”,说的也许就是这些钱吧。
触摸着侯伯宇用过的书桌,看着那些纸片和信件,我忽然觉得仿佛触摸到了他的呼吸和脉搏。
我要特别感谢侯伯宇的六弟侯伯文先生。他是位有心人,十多年前,便开始将父母、兄姊们谈话时说到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据说已有十多万字。在这本书的採访和写作过程中,我们多次见面,每次他都给我讲述一些二哥的往事,并且将他记录下来的部分文字资料拷贝给我。有时,他回想起一些往事也会马上打来电话给我讲述。有了那些丰富而又鲜活的细节,才使得本书中的故事真实生动起来。
2012年7月至10月底,採访和资料整理工作持续了三个月。收集到与侯伯宇相关的资料30多万字,整理採访录音近20万字,参看了可能涉及人物的传记、物理科普类书籍资料、时代背景资料超过200万字。就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人。那段时间我总在思考,为什幺曾感动了无数人的《哥德巴赫猜想》却没有感动侯伯宇以及他的中科院同事们?在熟悉陈景润生活的人们眼中,“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为什幺会有如此大的差距?我要写出的侯伯宇,该是什幺样呢?屈奇曾对我说:“要写出一个真实丰满的人,不仅要感动无数没见过他的人,也要感动那些熟悉他的人。你要努力走进一个科学家的世界,还要站在当时的社会坏境中看待和理解那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三个月中,採访了几十位侯伯宇的亲友、同事和学生。有人说,他是个不谙世事的书呆子,也有人说,他是事事了然于心的明白人;有人说,他讷于言表,也有人说,他语锋尖锐;有人说,他毫无生活情趣,也有人说,他极其讲究生活品质。每个人看到的侯伯宇似乎都不一样。他所坚守的很多方面和现实社会有着难以化解的冲突,他曾试图有所改变,却不能跳出自己行为準则的“牵绊”。在这样的準则之中,他只能像一个倔强的粒子,固执地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当我将他回置于所经历过的时代之中,他的所有行为和思维方式都有了合理性和逻辑性,那是一个时代造就出的逻辑。
但真正开始写作时,依然觉得艰难。侯伯文对我说,他曾问二哥,评院士的事情是否需要帮忙,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关係做些工作,可二哥却皱起眉头说:“你不要害我!”这句话时常会出现在我脑海,心中存着这份敬畏,落笔时更加小心翼翼。
这本书的写作中,最大的困扰便是如何将侯伯宇所从事的研究用通俗的方式写出来。我曾经向所有採访过的物理学者询问,但他们都说,对于非专业的人而言,这些东西很难理解。有一位侯伯宇的学生说:“西大宣传部曾让我通俗地写一点儿侯老师研究领域方面的内容,这太难了。”他递给我一摞资料,“这是我能写出的最简明的说明,你要是能看懂就拿去用吧。”我接过一看,第一页开始便是天书般的公式,只能放弃尝试,悻悻地递还给他。我还得到了一本《侯伯宇文集》,集结着侯先生髮表的所有我看不懂的论文,后记中虽然有些论述性的文字,但同样夹杂着大量的公式。他的另一位学生说:“侯老师故意把这些文字写得只有专业的人才能看懂。”
对于採访过的那些学者,我丝毫不怀疑他们的专业能力,只是他们不习惯用通俗的语言讲述自己专业的工作。这让我想起一句话,“上帝什幺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有这种表达方式。”
美国着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理察·费曼(Richard Feynman)曾在巴西做过一次演讲。他举起一本在巴西公认写得非常好的物理教科书,“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实验结果。随便把书翻开,指到哪一行,我都可以证明书里包含的不是科学,而只是生吞活剥的背诵而已。”费曼随手翻开一页,念道:“摩擦发光:当晶体被撞击时所发出的光……”他说:“这样的句子,是否就是科学呢?不!你只不过是用一些字说出另一些字的意思而已。有没有看到过任何学生回家试着做个试验?我想,他没有办法做,他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做。但如果你写:‘当你在黑暗中用钳子打在一块糖上,你会看到一丝蓝色光。其他晶体也有此效应,没人知道为什幺。这个物理现象被称为摩擦发光。’那幺就会有人试着回家自己做,这就是一次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更有人说,“没有物理修养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如果我们看到的物理不仅仅是那些繁难的公式,而是费曼所描述的那种“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会不会有更多的青少年爱上物理,爱上科学? 我尝试着用通俗的方式描述侯伯宇的工作,但毕竟对物理的了解过于肤浅,如果有失误之处,还望读者予以指正并谅解。其实,我更希望有一天能看到物理学家用轻鬆易懂的语言给我们讲述物理世界的奥秘。
这是一次困难重重的写作,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地将写好的某段稿子传给屈奇过目,很多时候,得到的评价是: “能不能再改一下……”被他如此反覆地“折磨”,我嘴上说“好吧”,心里却满是怒火,每次退出和他的连线后,我都会撕开一袋曲奇饼乾,恶狠狠地咬掉几块。
在我每天忙于採访、写作的那段日子里,极少有时间陪伴和照顾怀孕的妻子,她却没对我说过一句怨言。父母先后入院手术,怕打断我的工作而瞒着我,陪护的事情都是姐姐哥哥承担。我要感谢亲人们的支持。2012年12月26日,儿子降临人世,岳母从外地赶回来,帮我们照顾孩子。那段时间,正是我的写作最为艰难的时候,怎幺写都觉得不好,我决定给自己三天假,陪伴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儿子还没有名字,妻子说:“你不会等到这本书写完才有时间起吧?”那三天我绞尽脑汁,最终决定叫他“书畅”,妻子笑了:“你是想让这本书写得顺畅些是吧?”这纯属巧合!其实,妻子名叫申易,合起来是个“畅”字。
经过六次大改和难以计数的小改之后,这本书终于可以交稿了,我已经用尽所有的力气。屈奇说:“还不错,但跟咱们当初想达到的目标还是有点儿差距。”我很清楚他这话说得没错,但我还是忍不住又想去吃几块饼乾。
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曾写过一首浪漫的小诗:
To see aworldin a grain of sand, 从一粒沙看见世界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从一朵花知道天宸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yourhand 用一只手把握无限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用一剎那留住永恆
侯伯宇用毕生精力,希望通过那些看不见的粒子解开自然界的奥秘,如同“从一粒沙看见世界”;我用近一年的时间,希望通过他的经历了解那个时代,如同“从一朵花知道天宸”。虽然我们所做的事情相差万里,但我们相同的是,希望“用一剎那留住永恆”。只是,这个过程一点儿也不浪漫。
2013年4月26日
序言
谢谢你翻开这本书!也许你是因为侯伯宇的名字而来,也许是因为书名有点儿科幻色彩而来,也许只是百无聊赖地信手一翻,但无论因为什幺,我都要感谢你!
我相信在没有读完这本书之前,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本书的主角侯伯宇是谁,他是乾什幺的,他有怎样的经历。
不知道侯伯宇并不奇怪。屈指算算,科学家中你能叫出名字的又有几位呢?我敢打一百块钱的赌,绝大多数人说不出高锟、崔琦、朱棣文、丁肇中是乾什幺的,虽然他们的研究成果足以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比如:高锟先生当年提出了“光纤通信”理论,如今网友们坐在电脑前享受宽频服务的便利才得以成为现实,但这并不能让人们像关注明星一样关心科学家的人生。我无意褒贬人们的趣味与偏好,也无意为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鸣冤叫屈,甚至我认为,如果希望侯伯宇和成龙一样家喻户晓,就如同期望在月球上开火锅店一样缺乏民众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许多科学家辛勤工作取得的科研成果,只是方便了我们更便捷地满足那些并不太高级的趣味与偏好的需求,而我们对那些创造了便捷的人却并不在意——高锟先生的“光纤通信”便是例证之一。很多科学家终其一生都默默无闻,但他们依然在科研探索的道路上痛苦并快乐着,这是他们的宿命。
其实,写这本书之前,我跟你一样,没听说过侯伯宇的名字。我还必须承认,此前我对其他的科学家也同样毫无兴趣,这种迴避的态度源于曾看过的一些科学家生平传记类的文章,那种“制式”的写法,让我一度误认为科学研究、发明创造是“枯燥”、“无趣”与“苦不堪言”的代名词,是“屌丝”、“呆子”们的智力游戏。当我半推半就地接下了这本书的写作任务,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去了解侯伯宇、了解他周围的那些科学家后才发现,原来,科学家的世界有着如此令人着迷的魅力。于是我才恍然大悟,并非科学和科学家无趣,而是写科学家的那些文字实在乏味,导致我们对科学家的想像被引入了多幺不靠谱的方向。
话题好像跑偏了,我们还是说说本书的主角侯伯宇吧。
侯伯宇是西北大学的教授,是一位在理论物理学界名声响亮的人物。他曾与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有过愉快的长期合作,并且与其中两位——杨振宁和李政道保持着长达数十年的友谊。他受杨振宁邀请赴美交流期间,发表了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侯氏变换”的研究成果,他还协助李政道先生创立了CUSP队考试(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画),促成建立中国的博士后制度的工作。他曾是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发表了200多篇论文,与数十位国际一流的物理学家有过良好的合作交流,在国际、国内物理学界有着极高的声望。
但这不是他的全部。
有人说,他是个除了工作没什幺爱好的人,这似乎很符合我们惯常对科学家性格的想像,却同样不是他的真面目,这只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四维空间”表象。在现代物理学家眼中,我们的世界并非只是由长、宽、高三个维度再加时间维度组成,而是一个奇妙的蜷缩在一起的十一维空间。本书名为《十一维空间》,并非仅仅因为那是侯伯宇最终的研究领域,而是为了表述这位科学家的多维人生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侯伯宇就如同一个蜷曲着的十一维空间,他将自己柔肠寸断的内心世界紧紧地包裹起来,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只会拚命工作的倔强老头,一副看似不近人情的冷麵,而忽略了他的极为丰富而複杂的多面人生。然而那些被压在内心的过往,总是对他的言行施加着影响,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内心最深处的空间会瞬间打开,释放出惊人的力量,又迅速“塌缩”回原来的状态。我所做的就是抓住他打开内心的那些瞬间,走进他的世界。这是一次重新发现的过程。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又何尝不是一个十一维空间呢?
我想,还有人会问,侯伯宇从事的物理工作到底是研究什幺的?
这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超级问题,如果让我对此做出全面、準确的回答,就相当于让我在三米跳板上做出309B,那可是难度係数达到4.8的最高难动作,目前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做出来,但那个人不是我。我只能用难度係数连0.00048都无法达到的方式向你略述什幺是理论物理,好在本书并不是讲学术,这样的难度係数足够帮助我们理解侯伯宇所从事的工作了。
侯伯宇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从事物理研究,那时最前沿的研究方向是“粒子物理”。那时候的物理学家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几种或者是一种微小到用肉眼无法看到的基本粒子构成,他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粒子,并搞清楚它们是怎样运动的,以及这样的运动方式会造成什幺结果,最终使世界呈现出我们见到的这般模样。中学时,我们就学过分子、组成分子的原子,以及组成原子的电子、质子和中子,科学家们认为还可以再这样细分下去,直至找到最终的那个粒子。但他们沮丧地发现,他们找到的粒子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甚至达到了300多种。
问题是,物理学家们怎样才能发现那些看不见的粒子呢?
很多人脑海中浮现出的物理学家的形象也许会是这样的——头髮凌乱,有些神经质的老男人,穿着白大褂站在一檯布满了按钮、手柄和仪表的庞大仪器前,口中念念有词地扳下手柄按下按钮,几道刺眼的闪电之后诞生了一个奇蹟——好莱坞电影中,科学家往往都是这种未来战士的形象,虽然有些概念化,但大致的情形也不错。物理学家们操纵着比电影中更为庞大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仪器,发现了前面所说的那300多种粒子的存在。
不过,并不是所有物理学家都是这样工作,这种“未来战士”式的工作方式被称为“实验物理”。还有另一种称为“理论物理”的研究方式,依靠複杂严谨的数学计算,推算出那些看不见的粒子,并且用数学公式描述它的大小和运动方式。侯伯宇便是用这种方式进行物理研究,很显然,这种工作方式比实验物理省钱得多,几张纸一支笔就可以进行,看上去就像个乡村会计。不要因为这种工作方式过于“简陋”就小看理论物理,在物理研究中,“未来战士”和“乡村会计”必须相互验证,缺一不可。
侯伯宇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的研究方向从粒子物理转向了超弦理论,这是目前物理学界中最前沿的领域。超弦理论完全颠覆了以前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的物质是由粒子组成的观念,认为那些以前被当作粒子的微小物质其实是不断振动着的“弦”,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只是因为振动方式不同而已。 超弦理论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更为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你所感知的长、宽、高再加时间的四维空间,而有着超出你想像的更多空间——多达二十六维。只不过,多出的这些空间,你看不见,其中十五维被“压实了”,剩下的十一维空间中,有四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立体空间,另外七维蜷曲在一个极小的複杂空间内——大约为1毫米的两千五百四十万亿亿亿分之一的空间,我们根本无法觉察到这幺小的尺度,科学家们也没法解释为什幺它们非得把自己搞成那样。这些蜷曲的空间维只有在极高的能量状态下才能打开,而且打开后也不能稳定,仍会坍塌成原来的那种状态,只剩下我们所感受到的三个空间维和一个时间维。
大多数时候,我们确实难以分清说出惊世骇俗言论的那个人到底是疯子还是科学家。即便在物理学界,这种理论也并非人人都能接受,当这一理论刚刚出现的时候,包括侯伯宇在内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曾经认为,这只是个不能为实验结果所证实的假说,一度对其抱有怀疑态度。
虽然“超弦理论”以及由它发展而来的“M理论”看上去如此不可理喻,但它们还是成为目前国际物理学界最热门、最主流的研究方向,世界上众多顶级物理学家都在从事着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大约在2000年,侯伯宇也由最初的怀疑,转变为对“M理论”的关注,并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方向,最终投入对它的研究工作。他认为如果攻下这一研究课题,将会突破困扰物理学界多年的发展瓶颈,物理学可能由此而发生一次重大的飞越。
其实,侯伯宇也曾经名噪一时。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学界在一次伟大的变革中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托转型时代的福,不少过去鲜为人知的科学家突然成为社会知名人士,比如华罗庚、陈景润就像今天许多明星一样引人注目。侯伯宇在那个年代,也声名远扬,被新华社以《中国的骄傲》为题进行报导,即便物理圈外的很多人也知道这位着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但后来,他觉得那种“戴高帽”的宣传方式,往往在熟悉的人中成为笑谈,甚至为同行所忌惮造成工作上的不便,因而开始拒绝媒体的採访,主动地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再后来,随着“科学的春天”逐渐远去,媒体也渐渐少了对科学家的报导,侯伯宇彻底将自己隐身于我们看不见的“多维空间”之中,以至于我这个在西安媒体圈内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讯息灵通”人士,此前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和事迹。
在一次次翻阅了那些已经发黄的档案后,在大量採访熟悉他的亲友之后,我甚至深感不安——儘管我们有忽略老实人的习惯,但侯伯宇却是绝对不应忽略的。
侯伯宇的中学同学丛林先生住在天津,他告诉我居住的小区位置,却不说楼层和房间号,80多岁的老人刚做完心脏手术,执意要亲自下楼来接我。这位传媒界老前辈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批新闻记者,从事新闻工作数十年,20世纪80年代他创办的杂誌《八小时以外》创下国内最高发行量。“你们要写侯伯宇,太好了!这样的人早就该写了。”他紧紧拉着我的手向家中走去,似乎害怕一鬆手我便会跑开再不回来。
客厅的桌子上码着一摞新旧不一的书,足有一尺多高。老先生用力将它们推到我面前:“我们重庆南开同学会有个内部刊物,刊登同学们的回忆文章或现在的近况,十几年了,出了这幺多本,你拿回去作为参考资料。我觉得可能有用的地方都做了标记,你找起来会方便些。”我拿起最上面的一本,随手翻开,里面多处都折着书角,折角的页面内,一些字句下用红笔蓝笔画着波浪线。我合上书页,手压在那摞书上对他说:“您放心,这些书我一定保护好,用完后马上给您寄回来。”他伸手压在我的手背上:“孩子,你听我说,这些书不用还。我已经80多岁了,还能有几个年头呢?我把它们送给你,希望你能写好那个时代,写好南开中学、写好侯伯宇,这些书才真的发挥出了最大的作用。”
侯伯宇的另一位中学同学朱景尧住在成都,也是一位新闻界的老前辈,他讲述了和侯伯宇一起经历过的颠沛流离的中学时代以及在政治风云中飘摇不定的青年时代。“你们这一代人赶上好时候了,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一定不要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再发生呀。”他说。
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的朱重远先生是侯伯宇的“同门师弟”,1963年两人一起考上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我们考入中科院后,第二年就开始搞‘四清’运动,就被下放到吉林的农村去搞‘四清’工作。”朱先生对我说,“一年后回来,我们一起参加建立层子模型的工作,只有大半年时间吧,工作刚完成就开始‘文革’,那以后就搞批判、搞运动,那时候连看书都可能被批判,谁还敢搞研究呢。老侯在中科院工作了十年,真正能搞研究的时间加起来也就是刚进去的那一年多。”他端起硕大的搪瓷缸喝了口茶,补上一句, “我们也一样。”讲述往事的过程中,朱先生时常会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可我觉得那笑声后面,是一丝苦涩和无奈。朱先生曾担任过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副所长,在国内外理论物理学界有着极高声望,和他的师兄一样,他也至今未能入选中科院院士,其中的原因他闭口不谈。
还有更多我採访过的侯伯宇当年的同事、合作者,他们讲述的那些侯伯宇所经历的往事,都是他们一同经历过的,那是一段沉甸甸的历史。一份责任感在我心中越来越重,我知道,这本书不仅是为侯伯宇而写,要写的是一代人的过往,是一代中国科学家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全面科学”的时代,连洗髮水都是各种“因子”、“分子”的成分。科学越来越值钱,身边的“科学”也越来越多,没几天就能出现一个新的“科学名词”,有人殚精竭虑编出些似是而非的伪科学概念,不过是为了让普通的玩意儿戴上“高科技”的高帽,能卖出个高价钱。
侯伯宇的六弟侯伯文对我说,他曾经问过哥哥:“你研究的这些东西什幺时候能套用?”侯伯宇沉吟片刻:“可能两百年后吧。”这句话让我感动,总有一些人,他们活着不是为了眼前的苟且,他们有梦想,那梦想不是“梦回唐朝”,也不是“锦衣玉食”,而是未来、是远方——这,也许才是我们应该有的中国梦吧。
记得那天结束了对丛林先生的採访,背着那摞厚厚的资料告别时,我说:“我一定会尽全力写出一个真实的候伯宇,写出你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坚持和信念。”老先生再次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另一只手在我手背上轻轻地拍打,低声说:“好……好……好!”
必须说明的是,2010年10月,80岁高龄的侯伯宇先生已因病去世,他生前所从事的可能改变物理学面貌的研究工作也因此未能完成。而他也因多年来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以及取得的突出成就,于2012年被追授为“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这正是我受命写这本书的原因。
这本书从侯伯宇的童年开始写起,也许有人会觉得,写一位物理学家花费这样的笔墨绕的圈子似乎有些远。但我认为,一个人童年开始所受的亲职教育,以及学校和社会环境影响的综合力是形成一个人性格的重要因素。侯伯宇和与他同龄的那一代科学家正在凋零,他们曾有着一份共同的坚守与梦想——为国家强盛而甘受艰辛。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仅为自己,更为这个国家。我希望通过描述侯伯宇的一生,重现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造就出的那一批人的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与其相参照,我们这一代人是否能将那份坚持与梦想更好地传承下去。
没错,这是一本模範人物的传记,不过,你不必担心会看到一个内容空洞的“高大全”式的英模人物故事,在这个已经被添加剂搞得满是疑惑的年代,我决定尽最大可能写出一个不含添加剂的“纯天然”的人,我相信,没有“添加剂”的产品,不仅“营养”足够丰富,“保质期”也会更长久些。
我很欣慰自己写下了这样一本书,记录下了科学界曾有过这样一批中国人。我无法确定会有多少人翻开这本书,所以我必须感谢现在打开这本书的你,哪怕只有你一个人记住了他们,这一代中国科学家就不会消失在历史的阴影里。
谨以此书献给我不曾谋面却最为熟悉的侯伯宇先生,以及那一代中国科学家。
我相信在没有读完这本书之前,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本书的主角侯伯宇是谁,他是乾什幺的,他有怎样的经历。
不知道侯伯宇并不奇怪。屈指算算,科学家中你能叫出名字的又有几位呢?我敢打一百块钱的赌,绝大多数人说不出高锟、崔琦、朱棣文、丁肇中是乾什幺的,虽然他们的研究成果足以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比如:高锟先生当年提出了“光纤通信”理论,如今网友们坐在电脑前享受宽频服务的便利才得以成为现实,但这并不能让人们像关注明星一样关心科学家的人生。我无意褒贬人们的趣味与偏好,也无意为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们鸣冤叫屈,甚至我认为,如果希望侯伯宇和成龙一样家喻户晓,就如同期望在月球上开火锅店一样缺乏民众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许多科学家辛勤工作取得的科研成果,只是方便了我们更便捷地满足那些并不太高级的趣味与偏好的需求,而我们对那些创造了便捷的人却并不在意——高锟先生的“光纤通信”便是例证之一。很多科学家终其一生都默默无闻,但他们依然在科研探索的道路上痛苦并快乐着,这是他们的宿命。
其实,写这本书之前,我跟你一样,没听说过侯伯宇的名字。我还必须承认,此前我对其他的科学家也同样毫无兴趣,这种迴避的态度源于曾看过的一些科学家生平传记类的文章,那种“制式”的写法,让我一度误认为科学研究、发明创造是“枯燥”、“无趣”与“苦不堪言”的代名词,是“屌丝”、“呆子”们的智力游戏。当我半推半就地接下了这本书的写作任务,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去了解侯伯宇、了解他周围的那些科学家后才发现,原来,科学家的世界有着如此令人着迷的魅力。于是我才恍然大悟,并非科学和科学家无趣,而是写科学家的那些文字实在乏味,导致我们对科学家的想像被引入了多幺不靠谱的方向。
话题好像跑偏了,我们还是说说本书的主角侯伯宇吧。
侯伯宇是西北大学的教授,是一位在理论物理学界名声响亮的人物。他曾与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有过愉快的长期合作,并且与其中两位——杨振宁和李政道保持着长达数十年的友谊。他受杨振宁邀请赴美交流期间,发表了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侯氏变换”的研究成果,他还协助李政道先生创立了CUSP队考试(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画),促成建立中国的博士后制度的工作。他曾是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发表了200多篇论文,与数十位国际一流的物理学家有过良好的合作交流,在国际、国内物理学界有着极高的声望。
但这不是他的全部。
有人说,他是个除了工作没什幺爱好的人,这似乎很符合我们惯常对科学家性格的想像,却同样不是他的真面目,这只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四维空间”表象。在现代物理学家眼中,我们的世界并非只是由长、宽、高三个维度再加时间维度组成,而是一个奇妙的蜷缩在一起的十一维空间。本书名为《十一维空间》,并非仅仅因为那是侯伯宇最终的研究领域,而是为了表述这位科学家的多维人生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侯伯宇就如同一个蜷曲着的十一维空间,他将自己柔肠寸断的内心世界紧紧地包裹起来,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只会拚命工作的倔强老头,一副看似不近人情的冷麵,而忽略了他的极为丰富而複杂的多面人生。然而那些被压在内心的过往,总是对他的言行施加着影响,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内心最深处的空间会瞬间打开,释放出惊人的力量,又迅速“塌缩”回原来的状态。我所做的就是抓住他打开内心的那些瞬间,走进他的世界。这是一次重新发现的过程。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又何尝不是一个十一维空间呢?
我想,还有人会问,侯伯宇从事的物理工作到底是研究什幺的?
这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超级问题,如果让我对此做出全面、準确的回答,就相当于让我在三米跳板上做出309B,那可是难度係数达到4.8的最高难动作,目前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做出来,但那个人不是我。我只能用难度係数连0.00048都无法达到的方式向你略述什幺是理论物理,好在本书并不是讲学术,这样的难度係数足够帮助我们理解侯伯宇所从事的工作了。
侯伯宇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从事物理研究,那时最前沿的研究方向是“粒子物理”。那时候的物理学家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几种或者是一种微小到用肉眼无法看到的基本粒子构成,他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些粒子,并搞清楚它们是怎样运动的,以及这样的运动方式会造成什幺结果,最终使世界呈现出我们见到的这般模样。中学时,我们就学过分子、组成分子的原子,以及组成原子的电子、质子和中子,科学家们认为还可以再这样细分下去,直至找到最终的那个粒子。但他们沮丧地发现,他们找到的粒子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甚至达到了300多种。
问题是,物理学家们怎样才能发现那些看不见的粒子呢?
很多人脑海中浮现出的物理学家的形象也许会是这样的——头髮凌乱,有些神经质的老男人,穿着白大褂站在一檯布满了按钮、手柄和仪表的庞大仪器前,口中念念有词地扳下手柄按下按钮,几道刺眼的闪电之后诞生了一个奇蹟——好莱坞电影中,科学家往往都是这种未来战士的形象,虽然有些概念化,但大致的情形也不错。物理学家们操纵着比电影中更为庞大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仪器,发现了前面所说的那300多种粒子的存在。
不过,并不是所有物理学家都是这样工作,这种“未来战士”式的工作方式被称为“实验物理”。还有另一种称为“理论物理”的研究方式,依靠複杂严谨的数学计算,推算出那些看不见的粒子,并且用数学公式描述它的大小和运动方式。侯伯宇便是用这种方式进行物理研究,很显然,这种工作方式比实验物理省钱得多,几张纸一支笔就可以进行,看上去就像个乡村会计。不要因为这种工作方式过于“简陋”就小看理论物理,在物理研究中,“未来战士”和“乡村会计”必须相互验证,缺一不可。
侯伯宇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的研究方向从粒子物理转向了超弦理论,这是目前物理学界中最前沿的领域。超弦理论完全颠覆了以前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的物质是由粒子组成的观念,认为那些以前被当作粒子的微小物质其实是不断振动着的“弦”,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只是因为振动方式不同而已。 超弦理论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更为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你所感知的长、宽、高再加时间的四维空间,而有着超出你想像的更多空间——多达二十六维。只不过,多出的这些空间,你看不见,其中十五维被“压实了”,剩下的十一维空间中,有四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立体空间,另外七维蜷曲在一个极小的複杂空间内——大约为1毫米的两千五百四十万亿亿亿分之一的空间,我们根本无法觉察到这幺小的尺度,科学家们也没法解释为什幺它们非得把自己搞成那样。这些蜷曲的空间维只有在极高的能量状态下才能打开,而且打开后也不能稳定,仍会坍塌成原来的那种状态,只剩下我们所感受到的三个空间维和一个时间维。
大多数时候,我们确实难以分清说出惊世骇俗言论的那个人到底是疯子还是科学家。即便在物理学界,这种理论也并非人人都能接受,当这一理论刚刚出现的时候,包括侯伯宇在内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曾经认为,这只是个不能为实验结果所证实的假说,一度对其抱有怀疑态度。
虽然“超弦理论”以及由它发展而来的“M理论”看上去如此不可理喻,但它们还是成为目前国际物理学界最热门、最主流的研究方向,世界上众多顶级物理学家都在从事着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大约在2000年,侯伯宇也由最初的怀疑,转变为对“M理论”的关注,并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方向,最终投入对它的研究工作。他认为如果攻下这一研究课题,将会突破困扰物理学界多年的发展瓶颈,物理学可能由此而发生一次重大的飞越。
其实,侯伯宇也曾经名噪一时。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学界在一次伟大的变革中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托转型时代的福,不少过去鲜为人知的科学家突然成为社会知名人士,比如华罗庚、陈景润就像今天许多明星一样引人注目。侯伯宇在那个年代,也声名远扬,被新华社以《中国的骄傲》为题进行报导,即便物理圈外的很多人也知道这位着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但后来,他觉得那种“戴高帽”的宣传方式,往往在熟悉的人中成为笑谈,甚至为同行所忌惮造成工作上的不便,因而开始拒绝媒体的採访,主动地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再后来,随着“科学的春天”逐渐远去,媒体也渐渐少了对科学家的报导,侯伯宇彻底将自己隐身于我们看不见的“多维空间”之中,以至于我这个在西安媒体圈内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讯息灵通”人士,此前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和事迹。
在一次次翻阅了那些已经发黄的档案后,在大量採访熟悉他的亲友之后,我甚至深感不安——儘管我们有忽略老实人的习惯,但侯伯宇却是绝对不应忽略的。
侯伯宇的中学同学丛林先生住在天津,他告诉我居住的小区位置,却不说楼层和房间号,80多岁的老人刚做完心脏手术,执意要亲自下楼来接我。这位传媒界老前辈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批新闻记者,从事新闻工作数十年,20世纪80年代他创办的杂誌《八小时以外》创下国内最高发行量。“你们要写侯伯宇,太好了!这样的人早就该写了。”他紧紧拉着我的手向家中走去,似乎害怕一鬆手我便会跑开再不回来。
客厅的桌子上码着一摞新旧不一的书,足有一尺多高。老先生用力将它们推到我面前:“我们重庆南开同学会有个内部刊物,刊登同学们的回忆文章或现在的近况,十几年了,出了这幺多本,你拿回去作为参考资料。我觉得可能有用的地方都做了标记,你找起来会方便些。”我拿起最上面的一本,随手翻开,里面多处都折着书角,折角的页面内,一些字句下用红笔蓝笔画着波浪线。我合上书页,手压在那摞书上对他说:“您放心,这些书我一定保护好,用完后马上给您寄回来。”他伸手压在我的手背上:“孩子,你听我说,这些书不用还。我已经80多岁了,还能有几个年头呢?我把它们送给你,希望你能写好那个时代,写好南开中学、写好侯伯宇,这些书才真的发挥出了最大的作用。”
侯伯宇的另一位中学同学朱景尧住在成都,也是一位新闻界的老前辈,他讲述了和侯伯宇一起经历过的颠沛流离的中学时代以及在政治风云中飘摇不定的青年时代。“你们这一代人赶上好时候了,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一定不要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再发生呀。”他说。
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的朱重远先生是侯伯宇的“同门师弟”,1963年两人一起考上了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我们考入中科院后,第二年就开始搞‘四清’运动,就被下放到吉林的农村去搞‘四清’工作。”朱先生对我说,“一年后回来,我们一起参加建立层子模型的工作,只有大半年时间吧,工作刚完成就开始‘文革’,那以后就搞批判、搞运动,那时候连看书都可能被批判,谁还敢搞研究呢。老侯在中科院工作了十年,真正能搞研究的时间加起来也就是刚进去的那一年多。”他端起硕大的搪瓷缸喝了口茶,补上一句, “我们也一样。”讲述往事的过程中,朱先生时常会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可我觉得那笑声后面,是一丝苦涩和无奈。朱先生曾担任过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副所长,在国内外理论物理学界有着极高声望,和他的师兄一样,他也至今未能入选中科院院士,其中的原因他闭口不谈。
还有更多我採访过的侯伯宇当年的同事、合作者,他们讲述的那些侯伯宇所经历的往事,都是他们一同经历过的,那是一段沉甸甸的历史。一份责任感在我心中越来越重,我知道,这本书不仅是为侯伯宇而写,要写的是一代人的过往,是一代中国科学家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全面科学”的时代,连洗髮水都是各种“因子”、“分子”的成分。科学越来越值钱,身边的“科学”也越来越多,没几天就能出现一个新的“科学名词”,有人殚精竭虑编出些似是而非的伪科学概念,不过是为了让普通的玩意儿戴上“高科技”的高帽,能卖出个高价钱。
侯伯宇的六弟侯伯文对我说,他曾经问过哥哥:“你研究的这些东西什幺时候能套用?”侯伯宇沉吟片刻:“可能两百年后吧。”这句话让我感动,总有一些人,他们活着不是为了眼前的苟且,他们有梦想,那梦想不是“梦回唐朝”,也不是“锦衣玉食”,而是未来、是远方——这,也许才是我们应该有的中国梦吧。
记得那天结束了对丛林先生的採访,背着那摞厚厚的资料告别时,我说:“我一定会尽全力写出一个真实的候伯宇,写出你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坚持和信念。”老先生再次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另一只手在我手背上轻轻地拍打,低声说:“好……好……好!”
必须说明的是,2010年10月,80岁高龄的侯伯宇先生已因病去世,他生前所从事的可能改变物理学面貌的研究工作也因此未能完成。而他也因多年来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以及取得的突出成就,于2012年被追授为“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这正是我受命写这本书的原因。
这本书从侯伯宇的童年开始写起,也许有人会觉得,写一位物理学家花费这样的笔墨绕的圈子似乎有些远。但我认为,一个人童年开始所受的亲职教育,以及学校和社会环境影响的综合力是形成一个人性格的重要因素。侯伯宇和与他同龄的那一代科学家正在凋零,他们曾有着一份共同的坚守与梦想——为国家强盛而甘受艰辛。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仅为自己,更为这个国家。我希望通过描述侯伯宇的一生,重现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造就出的那一批人的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与其相参照,我们这一代人是否能将那份坚持与梦想更好地传承下去。
没错,这是一本模範人物的传记,不过,你不必担心会看到一个内容空洞的“高大全”式的英模人物故事,在这个已经被添加剂搞得满是疑惑的年代,我决定尽最大可能写出一个不含添加剂的“纯天然”的人,我相信,没有“添加剂”的产品,不仅“营养”足够丰富,“保质期”也会更长久些。
我很欣慰自己写下了这样一本书,记录下了科学界曾有过这样一批中国人。我无法确定会有多少人翻开这本书,所以我必须感谢现在打开这本书的你,哪怕只有你一个人记住了他们,这一代中国科学家就不会消失在历史的阴影里。
谨以此书献给我不曾谋面却最为熟悉的侯伯宇先生,以及那一代中国科学家。
名人推荐
伯宇先生是国内着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数学物理研究,在场论拓扑性质研究、二维可积场研究、规範场理论、共形场统计模型、量子群等领域做出很出色的创新工作。他勤奋万分,以研究物理为自己人生理想。同时。他为祖国的人才培养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去世……是祖国物理事业的重大损失,我更是失去了一位多年的良友。
——李政道
——李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