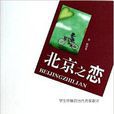《北京之恋:学生热棒的当代名家散文》收录了作者徐虹自2000年至2001年刊发在文学刊物及报刊中的散文作品数十篇,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温暖”的文字,反映了其在北京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北京之恋:学生热棒的当代名家散文》语言文字通顺流畅。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基本介绍
- 书名:北京之恋:学生热棒的当代名家散文
- 出版社:南京出版社
- 页数:216页
- 开本:16
- 作者:徐虹
- 出版日期:2013年11月1日
- 语种:简体中文
- ISBN:7553302716
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北京之恋:学生热棒的当代名家散文》由南京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徐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获第二届老舍散文奖、第二届冰心散文奖。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在《北京文学》《青年文学》《芒种》《钟山》《人民文学》《延河》《飞天》《小说月报·原创版》《黄河文学》《山西文学》等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约80万字。已出版散文随笔集《废墟之欢》《有内容的眼神》《上世纪的十七岁》《好像高雅》等。另有小说集《青春晚期》《徐虹中篇小说选》《夏日姐妹》等。散文曾入选《全国最佳散文选》《年度全国优秀散文选》等多种选本。
图书目录
第一辑北京断章
北京断章
消逝的朋友
玫瑰花般的早晨
十七岁
青春轶事
第二辑夜与昼
那座嘉陵江边的古城与我有关
诗人的夜晚和佞人的白天
在一座南方城市的24小时
厨房六则
哈瓦那之恋
第三辑凌乱的霓虹
四个姑娘
女生纪事
女人是城市的花朵
画廊
火车的怀旧情绪
仁慈之心
城市空心人
房子与自由有关
第四辑纸上男女
以慢,以淡
淡水太阳
一生突围
英雄与流氓都在慢慢变老
人世之论
活着而且要活得好
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块玉
是树你就高高的
第五辑在远方
户外记忆版图
平遥的墙
走进一张邮票
在石头上看见时间
红蓝白,还有绿和咖啡色
北京断章
消逝的朋友
玫瑰花般的早晨
十七岁
青春轶事
第二辑夜与昼
那座嘉陵江边的古城与我有关
诗人的夜晚和佞人的白天
在一座南方城市的24小时
厨房六则
哈瓦那之恋
第三辑凌乱的霓虹
四个姑娘
女生纪事
女人是城市的花朵
画廊
火车的怀旧情绪
仁慈之心
城市空心人
房子与自由有关
第四辑纸上男女
以慢,以淡
淡水太阳
一生突围
英雄与流氓都在慢慢变老
人世之论
活着而且要活得好
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块玉
是树你就高高的
第五辑在远方
户外记忆版图
平遥的墙
走进一张邮票
在石头上看见时间
红蓝白,还有绿和咖啡色
序言
我们是城市的逃亡者
现在的都市,正像一只在瞬间膨胀起来的气球,它的心儿只有指甲盖那幺一点点。或者它根本就没有心儿,有的只是被催情的草莓、机器养出来的冷冻鸡、注水的西瓜,还有那些裁剪得体的空心人……确时候我坐在房间一角,一手抵住下颌,冷冷地朝向地毯上的某一朵花,即刻会陷人人生的最迷局。眼里的世界在瞬间呈现一种荒诞和变形:人的中部宽大,四边向后退去,一个个尖头方脸,分明是怪异的表情。而我们,每一个人,仿佛都是这个时代的矛盾体:时髦,孤独,躁动,忘记自己心灵的来路,也逐渐忘记人生初始的目标,更忘记了那些遥远的温暖的存在。越是在热闹里,越是一个人——如果社会的大发展是以心灵的丢失为代价的话,真可谓买椟还珠。
我以为,但凡社会转型阶段必然经历一段精神的兵荒马乱、信仰的分崩离析、道德的无所适从。中国社会自现代史以来,不肖说远景的历次战争以及各种运动,单说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腰斩、道德的蹂躏姦杀、信仰信任的毁灭和侮辱,其破坏性的效果就是颠覆性的。改革开放30年的超速发展,那些被束缚的筋骨得以舒展,但是,也使得中国的都市文明在自我重构和外来影响中消化不良、变形和夹生。旧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健全,在这个道德空气稀薄的状态中的人们难免迷失和窒息。这一切作用于现代都市人的个案之中,都使我们病态,不健全,没有心灵归属,幸福指数不高——挣钱和不挣钱、结婚和不结婚、美丽与不美丽,升职和不升职,怎样都不能快乐。我们找不到心灵居所,我们逐渐失去安稳的能力,我们正在从一个地方逃往另一个地方,然后真正到了另一个地方,又觉得不知所以,继续接着从另一个地方再跳转到新的地方。每一个都不是我们要寻找的所在。我们的心灵,正在成为可怜的失魂落魄的逃亡者和流浪者。
也正因如此,那些值得记忆的往昔与往昔中温暖的存在,便更会顽强地不期而遇地如梦幻般时时闪现。记忆的零星的碎片,会在某一个夏天的某一个没情没绪的下午,在头脑的角角落落里,忽然浮现又忽然消失。是回望的风把它们吹醒了。如同平静的湖水骤起涟漪,苍白的旧日起死回生,一个毫无姿色的女人忽然堕入爱情——时间迅速地朝前走了,审美的过程却是略有滞后的。因此那些零星而温暖的存在,在记忆的深处层层浮现开来,形成文字之花一朵一朵地开放。
遥远的声响在很远处零散地跌落,如金色的铃,一簇一簇,满天飘飞,丁零脆响。它们储存于我的记忆那幺久,却曾经无知觉地静默和潜伏。它们像柜子底的那件滚着金边的暗紫旗袍,全盛时代已经过去,式样老旧,溢彩流光。
感谢虚构和记忆。它们是我们在流亡的灵魂的诺亚方舟。
因此在这里呈现给读者的,基本上是2000年至2001年我刊发在文学刊物及报章中的散文作品。如果一定要说风格或者追求的话。那幺,温暖,是我所乐意形成的文字间的调子。它们可以被理解为“都市散文”这一宏大构架之间的散乱而零碎的材料。它们或许彼此之间有关联性,但是在结构上还是独立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写作第一篇文学作品前的冲动:大约1997年,那时我27岁,在参加一个杂誌社的郊外沙龙的回城公共汽车上,正是傍晚时分,看着外面土黄色的沙尘暴。那时候我正是人生起飞要征服世界的年龄,想着一切皆有可能的前程,以最大的肺扩量把最远处的气体吸进身体,觉得自己能量充实、无所不能,简直可以变成随时飞行的超人,激动得浑身战慄。路边一棵棵树因为速度而虚化成了横线条,往远处去,又成为孤绝而独立的剪影,在凝重的暮色中慢慢变成绛色,仿佛我人生未来的路标与暗示——那一年冬天的味道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是后来四季的风从不同的方向吹,总也吹不来那一次的气息……
有时候我会想:写作是什幺?文学又是什幺?在我看来,文学与写作正是将每一个平凡的灵魂的不同凡响的人生经验,在艺术化的通道中经过浸染、过滤与修裁之后呈现的精华与真相。它是对心灵由表及里的深层触动,也是灵魂深处曲折表意的长线传达。最好的文学代表自己也代表他者。在自我发现中也可以发现他者。在他者内心中可以找到自己的共鸣和呼应。因此“我”并非单纯的“我”,“我”即是社会某一局部的缩影。正是基于这点认识,我期待将青春与生命的经验用文字零星记录。或许这件事对世界来说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证词,让我怀着敬畏之心。
在文学阵营中我自然尚属年轻一辈。有幸与这幺多前辈、师长共同出书是我多年以前的梦想和奢望。以文学的名义,站在他们中间我感到光荣!他们对于文学的贡献有目共睹,举足轻重,值得研究。特别需要感谢刘孝存老师的热情扶持和精心指点。正像朋友们所说,他除了以特有的灵性与坚持为文学作作出杰出贡献,如创作长篇小说、研究及评论长篇小说之外,更对年轻人深怀“惜才之心”——此处并非强调“才”而是强调他的“惜”。没有他的帮助和联络,不可能有这本书。在此特意致谢。
徐虹
2012年2月于北京世纪城寓所
现在的都市,正像一只在瞬间膨胀起来的气球,它的心儿只有指甲盖那幺一点点。或者它根本就没有心儿,有的只是被催情的草莓、机器养出来的冷冻鸡、注水的西瓜,还有那些裁剪得体的空心人……确时候我坐在房间一角,一手抵住下颌,冷冷地朝向地毯上的某一朵花,即刻会陷人人生的最迷局。眼里的世界在瞬间呈现一种荒诞和变形:人的中部宽大,四边向后退去,一个个尖头方脸,分明是怪异的表情。而我们,每一个人,仿佛都是这个时代的矛盾体:时髦,孤独,躁动,忘记自己心灵的来路,也逐渐忘记人生初始的目标,更忘记了那些遥远的温暖的存在。越是在热闹里,越是一个人——如果社会的大发展是以心灵的丢失为代价的话,真可谓买椟还珠。
我以为,但凡社会转型阶段必然经历一段精神的兵荒马乱、信仰的分崩离析、道德的无所适从。中国社会自现代史以来,不肖说远景的历次战争以及各种运动,单说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腰斩、道德的蹂躏姦杀、信仰信任的毁灭和侮辱,其破坏性的效果就是颠覆性的。改革开放30年的超速发展,那些被束缚的筋骨得以舒展,但是,也使得中国的都市文明在自我重构和外来影响中消化不良、变形和夹生。旧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健全,在这个道德空气稀薄的状态中的人们难免迷失和窒息。这一切作用于现代都市人的个案之中,都使我们病态,不健全,没有心灵归属,幸福指数不高——挣钱和不挣钱、结婚和不结婚、美丽与不美丽,升职和不升职,怎样都不能快乐。我们找不到心灵居所,我们逐渐失去安稳的能力,我们正在从一个地方逃往另一个地方,然后真正到了另一个地方,又觉得不知所以,继续接着从另一个地方再跳转到新的地方。每一个都不是我们要寻找的所在。我们的心灵,正在成为可怜的失魂落魄的逃亡者和流浪者。
也正因如此,那些值得记忆的往昔与往昔中温暖的存在,便更会顽强地不期而遇地如梦幻般时时闪现。记忆的零星的碎片,会在某一个夏天的某一个没情没绪的下午,在头脑的角角落落里,忽然浮现又忽然消失。是回望的风把它们吹醒了。如同平静的湖水骤起涟漪,苍白的旧日起死回生,一个毫无姿色的女人忽然堕入爱情——时间迅速地朝前走了,审美的过程却是略有滞后的。因此那些零星而温暖的存在,在记忆的深处层层浮现开来,形成文字之花一朵一朵地开放。
遥远的声响在很远处零散地跌落,如金色的铃,一簇一簇,满天飘飞,丁零脆响。它们储存于我的记忆那幺久,却曾经无知觉地静默和潜伏。它们像柜子底的那件滚着金边的暗紫旗袍,全盛时代已经过去,式样老旧,溢彩流光。
感谢虚构和记忆。它们是我们在流亡的灵魂的诺亚方舟。
因此在这里呈现给读者的,基本上是2000年至2001年我刊发在文学刊物及报章中的散文作品。如果一定要说风格或者追求的话。那幺,温暖,是我所乐意形成的文字间的调子。它们可以被理解为“都市散文”这一宏大构架之间的散乱而零碎的材料。它们或许彼此之间有关联性,但是在结构上还是独立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写作第一篇文学作品前的冲动:大约1997年,那时我27岁,在参加一个杂誌社的郊外沙龙的回城公共汽车上,正是傍晚时分,看着外面土黄色的沙尘暴。那时候我正是人生起飞要征服世界的年龄,想着一切皆有可能的前程,以最大的肺扩量把最远处的气体吸进身体,觉得自己能量充实、无所不能,简直可以变成随时飞行的超人,激动得浑身战慄。路边一棵棵树因为速度而虚化成了横线条,往远处去,又成为孤绝而独立的剪影,在凝重的暮色中慢慢变成绛色,仿佛我人生未来的路标与暗示——那一年冬天的味道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是后来四季的风从不同的方向吹,总也吹不来那一次的气息……
有时候我会想:写作是什幺?文学又是什幺?在我看来,文学与写作正是将每一个平凡的灵魂的不同凡响的人生经验,在艺术化的通道中经过浸染、过滤与修裁之后呈现的精华与真相。它是对心灵由表及里的深层触动,也是灵魂深处曲折表意的长线传达。最好的文学代表自己也代表他者。在自我发现中也可以发现他者。在他者内心中可以找到自己的共鸣和呼应。因此“我”并非单纯的“我”,“我”即是社会某一局部的缩影。正是基于这点认识,我期待将青春与生命的经验用文字零星记录。或许这件事对世界来说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证词,让我怀着敬畏之心。
在文学阵营中我自然尚属年轻一辈。有幸与这幺多前辈、师长共同出书是我多年以前的梦想和奢望。以文学的名义,站在他们中间我感到光荣!他们对于文学的贡献有目共睹,举足轻重,值得研究。特别需要感谢刘孝存老师的热情扶持和精心指点。正像朋友们所说,他除了以特有的灵性与坚持为文学作作出杰出贡献,如创作长篇小说、研究及评论长篇小说之外,更对年轻人深怀“惜才之心”——此处并非强调“才”而是强调他的“惜”。没有他的帮助和联络,不可能有这本书。在此特意致谢。
徐虹
2012年2月于北京世纪城寓所